長篇紀實《潛流》由廣東省作協殘聯分會會長王心鋼、韶關市作協主席榮笑雨和國家二級作家李迅共同創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華南抗日戰場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詩性作品,涉及的歷史事件主要有廣州淪陷、韶關成為戰時省會,兩次粵北會戰,香港營救文化人、東縱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點塑造了紅色省委書記張文彬烈士的光輝形象,人物有血有肉,豐滿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現實主義之上的傳奇想象,富有情節性、故事性、傳奇性、可讀性。通過此書,讀者將真實了解到抗戰時廣東省委的烽火歷程,感受一代共產黨人為了民族解放的獻身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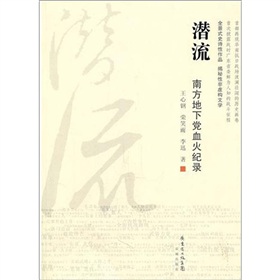
今天,讓我們來品讀《潛流》第九章:殺機重重。
1
南方的夏天說變就變。中午還是烈日當頭,晴空萬里,臨近黃昏,卻是烏云密布,樹葉紋絲不動,山谷里各種鳥兒煩躁地叫著。此時,在通往江西吉安縣城的一條逶迤山路上,松木蔥蘢,茅草叢生,不遠處急急地走來四個收買山貨打扮的人。
走在前頭領路的是中共江西省委交通老鐵拐,他肩背大包袱,頭戴破草帽,身穿黑布衫,腳踏麻草鞋,猴頭瘦臉,滿面胡絡,邊走邊四處張望,像一個打短工的鄉下人。走在中間的是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他身穿藍布長袍,頭戴駝色禮帽,一副墨鏡恰好地掛在他那瘦長的臉上,儼然是個小老板。而他大步流星地走態,又暴露出他是個善于趕路的跋涉者。
后面緊隨的是省委宣傳部長駱奇勛和贛西南特委組織部長李昭賢,兩人都是伙計的打扮。接連趕了幾十里山路,駱奇勛文弱的身子已累得快要撐不住了,但他不敢喊聲歇歇,中統正四處抓共產黨,沿路布滿了明崗暗哨,不時夾雜著零星的槍聲。抬眼望去,遠處殘垣斷壁騰起縷縷青煙,一片蕭殺之氣。
自從告別方方后,謝育才攜妻子王勖到江西赴任。經過一個月的長途跋涉,于6月29日抵達江西吉安,這一天正好是農歷端午節,贛江上正在舉行熱鬧的劃龍舟比賽,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駱奇勛夫婦代表省委從山上下來迎接謝育才夫婦。王勖本是接任省委婦女部長的,但已近臨產。萬般無奈下,謝育才只好把王勖和駱妻兩人留在吉安城郊的省委統戰部長林鳳鳴家,自己于7月初,隨駱奇勛前往中共江西省委秘密根據地安福縣洋溪山上任。
其時,前任省委書記郭潛已離開江西、赴南委任職,由軍政部長顏福華代理書記,謝育才沒見到郭潛,感到有些遺憾。
顏福華代表省委機關歡迎謝育才的到來,并介紹說,省委機關除宣傳部長駱奇勛、統戰部長林鳳鳴和自己外,還有青年部長唐敬齋,宣傳干事周國君,另外,還有電臺長、報務員、武裝人員等。說著,遞上了郭潛撰寫的近三年工作報告。
謝育才于7月11日主持召開了有部分特委負責人參加的省委工作會議。會上,各特委負責人匯報了方方面面的情況,謝育才感到江西各地反共逆流空前猖獗,形勢十分嚴峻。
1940年前后,贛西南地區發生“吉贛泰事件”,國民黨特務在吉安、贛州、泰和等地的文化界、救亡團體及行政機關大肆搜捕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省委的基層組織遭到很大的破壞,其中湘鄂贛特委因無法工作于1940年撤銷,贛西北特委也于1940年11月遭到重大破壞。另外還有10多個縣委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打擊,黨員干部被捕約25O人,犧牲約150人。但前任省委書記郭潛在向中央和南委匯報工作中,夸大了江西黨組織的實際力量,沒有如實反映江西的真實情況,致使南委所制定的江西工作方針不完全切合實際。
令謝育才擔心的是,江西省委沒有按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的指示把武裝斗爭與秘密工作分開,轉入地下工作遲緩,在當前國民黨正掀起反共高潮的形勢下,這是十分危險的。就在省委工作會議上,謝育才果斷地決定將黨的組織與武裝斗爭分開,重新訓練干部,選派干部前往農村開辟工作。同時向南委發出了第一封電報,介紹了江西的情況。
在大埔南委機關,方方接到謝育才的電報后又喜又憂,喜的是謝育才一路安全,順利到達江西,憂的是江西形勢異常復雜,稍有不慎就會出事。次日,方方在與張文彬商量后,給謝育才復電,要他立即到廣東曲江,和那里的南委交通站聯系。
謝育才和省委其他領導商量后,決定省委機關仍由顏福華負責,自己先到吉安搞到路條之后再前往曲江,順便探看妻子。妻子身體一直很虛弱,他特托山上的同志打了些野味,給妻子補補身子。今天是7月15日,想著就要見到臨產的妻子,謝育才腳下的步子不覺加快了許多。
快到一個上坡處,老鐵拐停下來,回過頭說:“謝書記……不,老板,翻過一個坡就是吉安了,咱們到旁邊小竹林去休息一會,天黑后再下山,安全些。”
謝育才看看天,默想片刻,點點頭。
對于這個交通,謝育才總覺得有點說不出的滋味,才接觸了幾天,就發現他殷勤得有點過分,還時不時躲著自己的眼睛,像有什么心事,使人產生莫名的猜疑。憑著自己在閩西南從事游擊戰爭的多年經驗,交通一定要自己了解信得過的人。不過,自己剛來江西,情況還不熟悉,只好任由安排,也不好說什么。
四人朝小竹林走去。起風了,竹葉颯颯作響,頓生陣陣涼意,斜陽下的陰影更見山谷的幽深、神秘……
吉安,寓“吉泰民安”之意,是贛江中游的一個重要城鎮,這里地處羅霄山脈東端,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1939年3月24日,日寇占領南昌后,國民黨江西省政府遷至泰和,但仍以吉安為政治活動中心,豐城、樟樹至吉安一線由此成為水陸交通要道,云集了江西省許多政府機關、學校和商鋪,一時出現熱鬧繁榮的景象。
夏季,晝長夜短,到晚上7時多,天才漸漸黑下來。雖然是戰時,吉安仍是一片燈紅酒綠:達官、豪紳、閑客、軍官、傷兵、難民、野妓,再配上沿街的花燈、喧嘩的戲臺、囂鬧的叫賣聲,構成了戰時城鎮特有的風景。
夜總會前,霓虹閃爍,里面傳來“你這樣對我媚眼兒飛,害得我今夜不得安睡……”的歌聲,這是風靡上海各舞場的名曲《滿場飛》。相比起廣東的氣息,江西雖然毗鄰廣東,更風行的卻是上海的做派,連賣花小姑娘的叫賣聲也透著上海腔:“梔子花來哉?白蘭花——”西裝革履一副紳士派頭的男士這是自然不吝惜區區一毛錢買一朵白蘭花插在顯然是剛剛勾搭上的女人耳際,然后順手在女的臉上摸一把。街角處,一位算命的老先生守著冷清的攤檔,幽幽哼了一句戲腔:“大街上來了我要飯的人……”
老鐵拐領著謝育才三人熟門熟道地避開繁華大街,來到一條叫木匠街的僻靜小街。剛到街口。只見一輛輛國民黨軍車轟隆隆奔馳而過,揚起陣陣煙塵。他們幾人連忙躲到陰暗處。
老鐵拐低聲告訴謝育才:“這車是開往前線的。第一、二次長沙會戰連續被我中國軍隊打敗,駐武漢的日十一軍十分不甘心,又準備籌謀再攻長沙,為防止日軍從江西進入湖南,主要交通線國民黨軍已派重兵把守,并實施戒嚴,我們先找個客店歇歇腳吧,明天再去搞路條。”
謝育才壓低禮帽,說:“找個安全點的。”
早已餓得嘰嘰叫的駱奇勛,連忙隨聲附和,此時他恨不得有一桌子佳肴和一張大床,吃個大飽睡個痛快,而旁邊的李昭賢則一言不發,只是四處張望。
軍車過后,木匠街又恢復了平靜。這里,與其說是街,實際上是一條狹長的巷道,昏黃的街燈照射著青石板和鵝蛋石鋪就的路面,冷冷清清,偶爾有幾聲犬吠和孩子的哭聲……
老鐵拐指著對面一家小旅店說:“就住那間來福客棧吧,自己人開的。”說著便直奔而去,見謝育才還在打量,李昭賢接過謝育才手里的提箱:“一路也該累了吧,我們早點入住。”
這是一家中低檔客棧,門前掛著兩盞寫著“來福”二字的黃底黑字的大燈籠,它為雙層木樓建筑,樓板已發黑,人踏在樓梯上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樓下進門處,開著一間小食店,幾張八仙桌兩行排開,酒柜上擱著三只釉光透亮的酒壇。昏黃的燈光下,五六個食客正就著劣質白酒,大嚼鹵制的豬耳朵。干瘦的老板半倚在酒柜上,守著一臺破舊的留聲機,搖頭晃腦地打著拍子:“浮云散,明月照人來,團圓美滿今朝醉……”
老鐵拐熟門熟路地走過去,嚷著:“掌柜的,有客房嘛,要兩間,上好的。”
老板居然沒聽見,老鐵拐正想再叫他,謝育才攔住了沒讓叫,一直聽著這段電影版的《拷紅》放完。“……雙雙對對恩恩愛愛,著軟風兒向著好花吹,柔情蜜意滿人間。”雖然延安是明確反對這類靡靡之音的,但謝育才聽著時也不得不承認它的確撩人,否則這類“之音”也不可能攪動上海和半個中國的音樂市場。
唱片一停,那老板睜眼發現有人早就站在身邊,忙不迭賠禮:“失禮失禮,不知客官駕到。”
謝育才笑曰:“好曲會知音,老板好雅興。”
老板邊收唱片邊說:“的確迷人哪,周璇的歌就像豆腐做的刀子,割得你那個舒坦……哎呀扯遠嘍,老板住店?”
老鐵拐大聲道:“快給我們老板安頓好,兩間。”
老板見站在老鐵拐身后的謝育才派頭不小,忙不迭地關掉留聲機,說:“有,有,有。各位客官辛苦。”接著,他嘶聲歇氣地對著廚房喊:“小二,小二,來客人啦!快把客官帶到樓上東廂房去!”
一個愣頭愣腦的店小二跑了出來,二話不說,接過行李就把客人往樓上領。謝育才警惕地四下看了看,見無什么異常,便緊跟上樓。
老鐵拐在一旁吩咐老板:“掌柜的,有什么熟食,快點端上桌,外加一壇酒。”說完,“蹬蹬蹬”跑上樓。
店小二打開東廂房,把謝育才、駱奇勛和李昭賢讓進房,邊放行李邊說:“兩位客官,先請坐,我去打點熱水來。”
房子不大,但還算干凈,駱奇勛像散了架似地倒在床上,咕嚕著說:“走了兩天的山路,真是累人啦!”
謝育才摘下帽子和眼鏡,李昭賢遞過毛巾給他擦汗。
不一會兒,店小二推開門,提著一桶熱水進來,老鐵拐問:“酒飯好了沒有?”
“來了——”門外一聲應答,只見老板帶著幾個彪形大漢突然沖了進來,一把把烏黑的手槍對準了謝育才三人。
謝育才下意識地朝懷里掏槍,李昭賢卻搶先一步下掉了他的槍,并用槍頂住了他的腰脊:“不準動!”
謝育才愕然,震驚道:“老李,你……”
李昭賢的臉上露出陰險而得意的獰笑。“謝書記,恭候多時。“
謝育才好一會從牙縫里擠出兩個字:“叛徒!”
這時,墻上的大掛鐘“當當當”地敲了八下。
2
設下這個圈套的正是那個化裝成老板的人,他原名叫施平,化名莊祖芳、莊尚之,曾是少共中央交通處主任,叛變后死心塌地地為中統效勞,以“反共專家”自稱,現為國民黨中統局特種工作辦事處總干事兼贛南視察員。他臉形瘦削,眉毛黑濃,一對鷹隼的目光給人一種深不可測的感覺。
江西是革命老區,國共斗爭一直十分劇烈。紅軍長征后,國民黨仍然把江西視為共產黨的重點地區,特務統治更加強化。反共老手熊式輝在江西擔任省政府主席長達十多年,一手創立了江西地方特務組織“情報總站”和“保安處第四科”。中統特務總部在1934年12月也派來馮琦來江西擔任省調查統計室主任,接著又陸續調來一些老叛徒特務,如莊祖芳及施錦等人。軍統系統特務南昌組織也進一步加強為南昌站。不算江西地方特務組織,僅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系統在江西的職業特務到抗戰時期就各有7000多名。
1939年3月南昌淪陷后,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和省政府遷移至泰和縣。1940年3月,熊式輝經中統負責人朱家驊和軍統負責人戴笠同意,將中統江西省調統室、軍統的江西省站和本省地方特務組織江西情報總站、保安處第四科合并,在泰和成立江西省特種工作委員會,特委會由熊式輝自兼主任,成員包括省黨政軍警頭目,下設“江西省特種工作辦事處”(簡稱特辦處),作為具體工作機構,馮琦任主任,莊祖芳為總干事,在熊式輝的統一管轄下,集中力量對付共產黨。
吉安地區,曾是共產黨鬧“紅”鬧得最兇的地區,也是中共湘贛蘇維埃主席譚余保的游擊區。中統局把它列為反共重點區,特在江西設有兩個特務組織:一個是以章志純為主任的調查統計室,一個是以馮琦為主任的特種工作辦事處。莊祖芳上任后,成立了以李剛為隊長的中統行動隊,對積極抗戰的江西共產黨組織進行了多方面的破壞,捕殺了大批基層的共產黨員和愛國人士。但莊祖芳一直認為不解氣,他要求在國民黨統治區采取放長線釣大魚的策略,對共產黨江西組織給予徹底的破壞。
1940年底,他得到一條重要線索,在江西蓮花縣和湖南茶陵縣邊境界化垅汽車運輸檢查站上,檢查人員發現一對青年夫婦的行李中攜帶有中共書刊。經特辦處審查,男的叫張紹祖(又名張健行),曾擔任中共南昌市委領導人職務,女的叫許樾,是他的助手。莊祖芳聞之大喜,要手下將這對夫婦押往泰和縣,由他和馮琦親自輪流出面勸降。張紹祖夫婦最終辦了自首手續,寫了脫黨聲明,并暴露了中共吉安縣婦女支部書記萬國英的身份。莊祖芳迅速密令李剛逮捕萬國英。萬國英被捕后叛變,供出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黃路平之妹黃靜玲。
1941年6月1日,李剛在樟樹鎮密捕了黃靜玲。黃靜玲叛變后供認,她是中共贛西南特委的聯絡員,負責特委“吉安前方指揮站”至豐城、樟樹一帶的交通工作,領導人是楊道芬。莊祖芳于是設下圈套,要黃靜玲按原來的聯絡方式與楊道芬約定會晤地點。第三天,楊道芬約黃靜玲到吉安中山碼頭河邊一只柴船上晤面。
這只來往贛江上下流的柴船,本是中共流動的秘密聯絡點。在約定時間和地點,李剛帶領行動隊迅速包圍了該船,捕獲了楊道芬和全船中共男女干部黨員共17人。這不僅使中共贛江河流工作委員會和前方工作委員會遭到重大破壞,而且使中共江西省委在吉安的秘密交通站被破壞。
叛變后的楊道芬交代,他是中共贛西南特委宣傳部長兼吉安前方指揮部主任,省委書記陳然(即郭潛)已調南委,現新派了李志強(真名謝育才)任書記。最近,省委召開會議,贛西南特委組織部長李昭賢即將于明晨到達吉安,轉往省委開會。
莊祖芳喜出望外,立即釋放楊道芬。次日一早,在吉安電廠的楊道芬家中,李昭賢落入特務們的圈套。
李昭賢18歲當紅軍,身經百戰,在贛江流域有相當的號召力,莊祖芳知道,他一定掌握著比楊道芬更多的秘密,于是,軟硬兼施,終于撬開了李昭賢的嘴。李昭賢叛變后把藏在手電筒和牙粉盒下面的贛西南特委所屬全部黨組織、負責人及全部黨員名單全交了出來。
這樣,大破壞之門被打開。突出心戰,重用叛徒,上挑下連,控制組織,反用電臺,是特務在這次大破壞中的主要手段。
7月間,李昭賢按照莊祖芳的安排,沒有去省委機關開會,而是返回贛西南特委機關,謊稱省委讓他回特委,要特委書記黃路平自己去省委參加會議。黃路平不知其中有詐,于翌日下山。特委工作暫由李昭賢主持。于是,贛西南特委機關及其下屬組織完全被特務控制。
再說,黃路平在上了遂川縣城去吉安的長途汽車后,就被兩個持槍的特務一左一右夾在中間,動彈不得。車到泰和,他就被帶進了省調統室。在馮琦、莊祖芳的誘勸和威逼下,又看到李昭賢交出的全部名單,黃路平也叛變了,供出他所知道的省委情況和郭潛告訴他的南委在曲江(韶關)的一個通訊地址。馮琦認為他轉變態度好,馬上把他安置在特辦處編審組充當助理干事,以示獎勵。
李昭賢見狀,為表功,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說在柴船上抓捕的17人中,那個劃船的老頭可是不可忽視的人物,他真名叫蕭省三,化名老鐵拐,人稱老鐵,是一個1925年老共產黨員,現任省委交通。此次出現在船上,就是因為要帶李昭賢上山開會的。
李昭賢繪聲繪色解釋說,中共江西省委設在人跡稀少山路崎嶇的洋溪山中,沿途設有許多秘密報警的機關。劈開大毛竹,用筷子撐住,連接筷子的繩子又攔在路上。外人經過絆到繩子就會拉掉筷子,毛竹合并會發出一串響聲,一竹帶動一路,響聲就會逐步傳到省委駐地。要把省委書記謝育才騙下山,必須說服老交通老鐵拐合作,因為只有他才是唯一可以進入江西省委所在地洋溪山的人,如果沒有他的帶路。誰也上不了山。
莊祖芳一聽,倒吸了一口氣。他原以為這個其貌不揚的糟老頭是個普通人,打算關一兩年就把他放了,沒想到還是條有用的釣餌。
但說服老鐵拐叛變并非易事,他意志堅定,軟硬不吃。這讓莊祖芳有點手足無措。關鍵時刻,又是李昭賢出了個餿主意,說老鐵拐十分疼愛自己的獨子,視之為掌上明珠,只要抓住他的獨子,不怕老鐵拐不降。
果真老鐵拐見獨子被抓,軟了下來。莊祖芳為了試驗他是否真的轉變,還設計將老鐵拐三擒三縱,直到第三次被捕后,老鐵拐這才答應帶李照賢上山,去誘騙謝育才下山。但莊祖芳還是不放心,又讓老鐵拐、李昭賢、楊道芬三人宣誓簽字,拍照合影,并扣押老鐵拐的獨子為人質。
為了取得謝育才的信任,上山前,李昭賢特地找到王勖、駱妻,騙得了她倆寫給各自丈夫的信。上山后,老鐵拐也曾猶豫過,想向組織坦白。李照賢知道后威脅老鐵拐,你已經宣過誓為國民黨工作,說出來,只有死路一條,并以其獨子相威脅。
最后,老鐵拐一步一步地滑向深淵,終把謝育才騙下了山,由此有了本章開頭的一幕。
3
晚上9點,位于市郊的一間大院子里燈火通明。留聲機播出的軟綿綿的歌曲給布置得富麗堂皇的客廳平添一種迷離的氣氛。客廳對面鋪著紅地毯的餐廳,一陣陣誘人的酒肉香味不斷溢出來,在花草濃郁的院子里彌漫。只是,大門口雖掛著“尖兵半月刊社”牌子,卻站著兩排全副武裝的哨兵。當地人都知道,這里是江西中統特務的總機關,有名的“魔窟”。
這大院原是吉安的一個豪紳的私宅,第一次長沙會戰后,日軍戰機經常轟炸吉安,豪紳嚇得舉家搬到香港。莊祖芳就順手牽羊,把它占為己有,作為中統的辦公地點。平時,這里車水馬龍,常充斥著吉安上層達官貴人的談笑聲。而今天,主人只請一個客人——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
莊祖芳憑著與共產黨打交道多年的經驗,深知謝育才作為中共高級干部,自有其過人之處,嚴刑拷打,反使其意志堅強,應攻心為上,客家人有句俗話,叫做:“冷水泡茶慢慢濃。”
而駱奇勛是個文弱書生,一被抓就嚇得魂飛魄散,自然經不起兩打,于是他叫別動隊長李剛好好“招待”駱奇勛,讓他嘗嘗“辣椒水”,坐坐“老虎凳”,自己則陪謝育才優哉悠哉喝酒。
“來,謝先生,咱倆干一杯,兄弟我早仰先生大名,今天一見,先生竟是這么年輕有為,風流倜儻。”莊祖芳故作斯文態說著這不咸不淡的開場白。
謝育才一聲不吭,自被捕后他就決定盡量少說話,他清楚言過必失的道理。特務們正瞪大眼睛,伸長耳朵,捕捉他片言只語中的“價值所在”。他心中暗暗懊悔今天的大意。作為省委書記的他,更為擔憂的是,省委機關是否安全轉移,江西的地下黨組織有沒有遭到嚴重破壞……
他內心如焚,默默地望著窗外,不禁思念起了正在城郊的妻子和未見面的兒子。
“謝書記。”謝育才被一句熟悉的聲音打斷幻覺,他身邊陪坐的叛徒李昭賢。
李昭賢小心地勸道:“謝書記,走了一天的路辛苦了,來,吃菜,這道板栗煮鴨子是您最愛吃的,我特意為您做的。”
看著這昔日的部下,忽地變成一條沒有血性的癩皮狗,謝育才厭惡地把臉別到一邊。他不屑與叛徒坐在同一條板凳上!
這時一個特務悄悄地走到莊祖芳面前,耳語道:“姓駱的招了,說省委統戰部長林鳳鳴夫婦和謝育才的妻子就藏在城郊的省難童教養院,林鳳鳴的岳母林源是教養院院長。”
莊祖芳眼睛一亮,伸直了腰,定了一來,把手輕輕一揮,示意來人下去,然后堆起笑臉,對謝育才說:“謝書記,告訴你兩個好消息,一個是你的那個能言善辯的宣傳部長已同意跟我們合作了。”
“駱奇勛變節了?”謝育才心里一沉。
“謝書記是不是在想他變節了?不,不是變節,是棄暗投明。”莊祖芳邊說邊解開襯衣領扣,得意地夾了一大塊鴨肉往塞進嘴里大嚼起來,然后喝了一口酒,說,“這是四特酒,口感不錯,來吃菜,吃菜,別激動。還有一個好消息就是你很快就能見到你的夫人王勖、統戰部長林鳳鳴、李秀珊夫婦。來,為你們的團圓,干一杯!”
王勖,王勖真的被捕了?還有林鳳鳴夫婦?這是敵人用的奸計,還是剛才的幻覺應驗了?當看到駱奇勛被帶到門口,怯怯地低下頭不敢看人時,謝育才明白了,又一塊軟骨頭!
莊祖芳看了駱奇勛一眼,回過頭對李昭賢說:“老李,你和駱先生一起,坐我的車跑一趟,去把他們接來。記住,可別嚇著謝書記的美人兒喲!”
李昭賢獻媚地把腰一彎:“是,我一定照辦。”
謝育才目睹這一幕,氣得把一雙筷子折成兩截。
莊祖芳見狀,漫不經心地用毛巾抹抹嘴:“勤務兵,給謝書記換雙筷子,要鐵的。”
窗外,憋了大半天的雨終于嘩嘩地瀉下來,伴著雷鳴電閃,狂復仇似的,盡情地沖擊著、撕扯著這個破舊的城鎮。
黑色的陰謀,在猙獰的閃電中畢現騰騰殺機……
4
入夜,白日的高溫漸漸退卻,院子方有幾分涼意。夜風中,茉莉花散發出習習清香,竹節海棠盛開著絢麗的紅花,葡萄藤架上的濃密綠葉中,墨綠色的葡萄像一串串珍珠般懸掛著,令人垂涎欲滴。
莊祖芳沒心欣賞這盛夏美景。三天了,無論用盡什么酷刑,許下多少大愿,謝育才就是不肯開口。莊祖芳氣得把謝育才夫妻倆雙雙投進監獄。
監獄里,謝育才告訴王勖.敵人已完全了解他的真實身份。他只有以公開身份和敵人作堅決的斗爭。而王勖的身份并沒暴露,可作為家屬面目出現,避開政治問題,以利斗爭。果真,特務和叛徒一直認為王勖只是一個家屬,沒有強迫她提供黨的秘密。
7月30日,一聲啼叫,王勖在獄中生下一個瘦弱的男孩。莊祖芳便把王勖母子和謝育才關在一起,并假裝關心孩子,對謝育才、王勖勸說要為孩子的前途著想啊!謝育才幾句話把他頂了回去。
本來,謝育才被捕后,莊祖芳欣喜若狂,當即向上司寫出書面報告,說謝育才已捕獲。從他身上打開口子,不僅可以徹底摧毀江西的共黨組織,還可以破壞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然而,現在謝育才不吐真情,全面破壞中共江西省委的計劃就無法實現,莊祖芳吸著煙在院子煩躁地來回走著。
“莊視察員。”身后傳來沙啞的鴨公聲。莊祖芳翻了一眼,是李昭賢,他打心里就討厭這家伙,三天來,他出的餿點子連共產黨的邊也沒挨著,全頂屁用。
李昭賢知道莊祖芳反復無常,一不小心自己的小命就要丟在他的手中。這幾天他與駱奇勛商量了好久,總算想出一個主意,急忙來找莊祖芳:“莊視察員,我倒有一個辦法。”
“什么辦法?”莊祖芳心不在焉地說。
“中共江西省委機關在洋溪山,那里曾是紅軍根據地,且山高林密,大部隊去不易圍剿,容易打草驚蛇,我們不妨來個引蛇出洞。”李昭賢故作神秘地說。
“引蛇出洞?”莊祖芳來了興趣,停住腳步。
李昭賢四周望望,然后在莊祖芳耳邊如此這般嘀咕了一番。
莊祖芳想了想:“不錯,可以一試,不過要是出了什么岔子,我可唯你是問!”
“放心好了,我還等著領賞呢。”李昭賢一臉媚笑,心里卻罵:這個草包,有功就往自己頭上戴,有過則往別人身上推,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燈!
幾天后,省委交通老鐵拐來到了洋溪山。
洋溪山處于安福、永新、蓮花三縣交界處,這里山勢險峻,古木參天,常年云霧纏繞,人跡罕至,有的地方無路可循,只能順著溪澗或獸路而行,正是打游擊的好地方。此時,正是盛夏季節,草長林密,鳥鳴山澗。
顏福華出獵了。蔥綠的世界里,一只烏黑發亮的獵犬東拱拱西嗅嗅,草叢中時不時掠起一只羽毛絢麗的野山雉,或者嘣出一只黃乎乎的小野羊。
顏福華手起槍響,旁邊的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勤務員便連蹦帶跳地跑過去撿拾獵物,大聲嚷道:“顏部長,好槍法,再來一個!”
顏福華望著冒煙的獵槍,思緒卻回到那三年艱苦的游擊戰爭中……
在中共高級干部中,有兩個武林高手,一個是許世友,一個是譚余保,有“南譚北許”之稱。顏福華最敬佩的就是譚余保。譚余保是湖南茶陵人,人稱“茶陵牛”,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有人講他是共產黨的“程咬金”,他是中國第一個紅色根據地湘贛省的省委書記、省軍政委員會主席,被毛澤東稱之為“真正的農民領袖”。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后,湘贛蘇維埃主席譚余保帶領一支部隊留在這一帶堅持游擊戰爭。國民黨白匪軍和還鄉團嚷著:“人要換種,房要過火,石要過刀。”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并組織幾萬人的兵力封山燒山,企圖置游擊隊于死地。一些意志薄弱者下山向敵人投降,成了可恥的叛徒。這些叛徒中有原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陳洪時和原省保衛局長等人,他們帶著敵人四處捕殺共產黨人,給革命帶來巨大損失。
這天,譚余保擦拭著勃朗寧手槍,準備對叛徒、動搖分子大開殺戒,暗自發誓:“娘賣拐的,看哪個叛徒第一個闖到老子槍口上!”他在新成立的省委會議上決定成立肅反委員會,由特務隊長顏福華任肅反委員會主任。
顏福華長工出身,大高個,干瘦臉,兩眼充滿殺氣,寬大的皮帶上總交叉插著兩支德國造駁殼槍。他原是紅軍老三團的戰士,以武功好,槍法準,手段狠,打仗兇而倍受譚余保賞識,他帶領的特務隊員亦個個有一手好槍法和硬功夫。顏福華當上肅反主任后,堅決執行譚余保的命令,動搖者殺,叛變者殺。其隊員行動迅速、神秘,令特務和叛徒聞風喪膽。
不過,顏福華也是左得出奇的人物,常自作主張,以非常時期為由,錯殺了不少好人,一次還差點誤殺了大名鼎鼎的陳毅險些鑄成大錯。
1937年10月下旬的一天,四個人抬著一頂轎子來到九隴山地區游擊隊的一個崗哨前,轎子上走下一個大個子,頭戴禮帽,身穿長衫,腳穿皮鞋,前后左右還有一群國民黨衛兵,大個子打發走轎夫和國民黨衛兵后,自報家門叫陳毅,代表中共中央和國民黨談判,并拿出項英的介紹信,要求面見譚余保。
游擊隊員不信,認為他是特務或是叛徒,顏福華叫人拿來繩索兇狠地將陳毅捆個結實,吊在茅棚的柱子上。陳毅聽到茅棚里幾個負責人在研究決定要殺他時,急得高叫:“不能殺,你們殺掉我,要犯大錯誤的。”
譚余保從里間走了出來,聽陳毅講現在形勢變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火冒七竅:“我們共產黨人歷來講階級斗爭,你卻講階級合作,就是叛徒。”說著,就用銅煙管敲打陳毅的腦殼。
陳毅疼得淚水都要流出來了,叫道:“你有本事就講道理,打一個被吊半天的人算什么英雄?”
顏福華拔出槍嚷道:“對你們這號人,不但要打,還要殺!”
陳毅正言道:“你們不信,可下山看看,去找葉劍英和項英。”
還是譚余保明理,他阻止了顏福華的魯莽舉動,并派人按陳毅提供的地址,找到了新四軍駐吉安辦事處,證明陳毅果真是中共中央派來的黨代表。譚余保熱淚盈眶地對陳毅說:“對不起,把你吊了四天四夜,請你也把我吊四天四夜,贖罪吧!”
陳毅拍著自己的胸脯嗬嗬笑道:“我這個好同志,是個好同志嘛,譚主席,你警惕性高,斗爭堅決,做得對嘛!”
幾個月后,譚余保領導的游擊隊被改編成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1938年9月譚余保離開湘贛邊到延安出席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因病留在了延安。
想到這里,顏福華突然記起一件事,他把身邊的特務隊長譚冬崽拉到一邊,低聲說:“聽說譚主席臨走前,領著你和幾個貼身警衛員,秘密埋藏了錢物和一批槍支,作為戰略物資,告訴我那些東西藏在哪里?”
譚冬崽長得牛牯一般壯實,隆起的胸肌像上了釉似的,黑里透亮,針翹的短發,倒豎的濃眉,滿臉橫肉,說話洪亮,鏗鏘有聲,是個名副其實的猛張飛。他原是譚余保最信任的貼身警衛,曾多次出生人死、忠心耿耿地保護了譚余保,并在一次戰斗中丟了一只眼睛,成了“獨眼龍”。他憨厚地說:“譚主席說,這是黨的特級秘密,不能隨便告訴任何人。”
顏福華把手往腰里一插:“娘賣拐的,譚主席重病在身,不來了,現在我是省委代書記,游擊隊急于擴編,正等槍支和錢用,我以組織的名義命令你交出來!”
譚冬崽無奈,只好小聲地告訴顏福華埋藏地點。
顏福華滿意地點點頭:“好,好,不要再告訴別人。”
一陣山風吹來,譚冬崽不寒而栗,一種不祥的預兆油然而生……
“顏部長,顏部長,”一個戰士急匆匆地從山下跑來,“報告,顏部長,謝書記派來老鐵拐,說有緊急情況要見您!”
顏福華一揮手:“走,我們下山,你馬上把他帶到我的房間來。
顏福華剛洗完臉,老鐵拐就走進房里,笑著打了個招呼:“顏部長。”
顏福華一點頭:“坐吧。”
老鐵拐從黑布夾層里掏出一張小紙條說:“謝書記在吉安病倒了,這是他給您的親筆信,請過目。”
顏福華接過信細讀:
老顏:
我在吉安染病,不能上山。今上級有重要指示,請見信后火速來吉安,有要事商討,勿誤。
謝育才
7月18日
本來,這封信漏洞很明顯,既然有重大事情商量,謝育才應該自己回山,與省委其他同志集體研究,不應只要顏福華一人下山去“商量”。可是,山上的幾個省委負責人竟然誰都沒有看出問題。顏福華更是大老粗,未細看信,只是問:“謝書記他們還好吧?”
老鐵拐是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來這里的,臨行前,莊祖芳給了他一條黃金,說事成后重重有賞。他看到顏福華沒在意,這才松了一口氣,接過警衛員遞來的一勺水,美美地喝了一口:“謝書記,駱部長,林部長都好。嘿,謝書記的婆娘還生了一個胖小子呢,就住在吉安,謝書記可高興了。”
顏福華說:“這個老謝,真有福氣。好,老李,你休息一下,咱們晚上出發。”他回過頭囑咐警衛員把打來的野雉處理一下,帶下山給謝書記的妻子補補身子。
其實,對于謝育才的到來,顏福華心里有點不舒服,他原以為郭潛走后,這省委書記的位置應是自己的,誰知半路殺出個謝育才,一上任就風風火火的,公開在省委工作會議上,指責郭書記沒向上級全面反映真實情況,還說什么搞武裝工作的,要與秘密工作分開,批評江西黨組織的撤退工作不堅決,這不是針對自己嗎?娘賣拐的,幾個國民黨特務有什么好怕的,手里有槍,就公開與他們干。
當晚,夜黑風高,顏福華留下省委青年部長唐敬齋、宣傳干事周國鈞和少數武裝保衛隊員看守機關,自己親自從手槍隊里挑了五個精干隊員,由老鐵拐帶路,悄悄地下山。
在吉安城郊的一個大院子門前,老鐵拐用石頭篤篤地敲了幾下門,門“吱”地開了,李昭賢從里面出來,輕聲問:“來了?”老鐵拐點點頭。
隊伍進房后,李昭賢連忙握住顏福華的手:“顏部長,辛苦了,城里敵人在大搜捕,謝書記派我們來接應你們。快請。”
顏福華示意隊員警戒,李昭賢阻止道:“我已布置了崗哨,同志們走了一天的路,吃完飯好好睡一覺吧。”
駱奇勛從里房出來:“老顏快進來,我給你介紹一個人。”
顏福華撩開門簾,隨之進去,誰知一進門,一個麻袋迎面罩來,兩個黑大漢緊緊把他扭住,并下了他的槍。顏福華用力掙扎,大叫:“駱奇勛,你搞什么名堂?”
客廳里的手槍隊長聽見顏福華的喊聲,預料大事不好,把手中碗一摔,拔槍就往里屋沖。一個特務猛地從后面攔腰把他抱住。手槍隊長一個扛摔,把特務摜倒在地,隨手就是一槍。
“叭”地一聲,窗戶外伸入一支手槍,擊中手槍隊長的左胸。手槍隊長一咬牙,反手一槍,把暗算他的特務擊斃。
其他手槍隊員見狀,紛紛拔槍還擊。但院子已被特務包圍。“不準動,舉起手來!”墻頭窗外,一支支機槍、沖鋒槍對準了手槍隊員們。
手槍隊長手提兩把駁殼槍,邊打邊高喊:“往里沖,快救顏部長!”
里屋的門突然打開,兩個特務手提美式沖鋒槍一陣猛掃,一排子彈從手槍隊長的后背穿過前胸,鮮血噴涌而出,他側身倚在桌子上,想再打一槍,身子卻砰然倒下,兩只眼睛睜得通圓。寡不敵眾。五位手槍隊員三死兩傷。血浸透地下的青磚……
“好,干得漂亮。”大門猛地被撞開,莊祖芳帶領一批人馬闖了進來。他知道顏福華一行武功了得,特意從中統調來經過訓練的特種別動隊,并下了死命令:“活捉顏福華,其他的殺無赦!”
莊祖芳對著還在掙扎的顏福華說:“顏先生,別激動了,是我假冒你們謝書記的筆跡請你下山,共商剿共大計的。你看,你們的省委書記、宣傳部長、組織部長都到齊,就差你了,哈哈哈!”
旁邊的別動隊長李剛見兩位受傷的手槍隊員在血泊中掙扎,“叭叭”,就是兩槍,然后惡狠狠地踢了顏福華一腳:“這就是跟我們斗的下場!”
顏福華癱倒在地,悲恨地說:“娘賣拐的,老子一生豪勇,想不到今天在陰溝里翻了船!”
中共江西省委,這一經過多年嚴峻考驗的紅色政權,此刻卻在血雨腥風中,萬般驚險……
遠處,傳來夜貓子凄厲的叫聲。


掃一掃,關注廣東殘聯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