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起,作家王心鋼和韶關(guān)本地黨史專家梁觀福開始籌備創(chuàng)作長篇紀實《赤焰》。他們對北江工農(nóng)軍的歷史進行集中學習與研究。作為一支地方武裝的北江工農(nóng)軍,在中國革命危急關(guān)頭,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湘南起義,這在中國革命史上是罕見的,其征戰(zhàn)史亦可歌可泣。許多工農(nóng)軍英雄拋頭顱、灑熱血,將火熱的青春獻給了革命和人民,值得敬仰。《赤焰》把講述時間放在1927年4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前后,直到1928年4月“朱毛紅軍”會師,并重點介紹了周其鑒等革命烈士的背后故事。故事分為三大塊:
一是北江工農(nóng)軍是如何建立的,為什么要北上武漢,其中發(fā)生了什么;
二是北江工農(nóng)軍是如何參加南昌起義的,又是如何隨軍南下的,經(jīng)歷了哪些戰(zhàn)斗;
三是南昌起義失敗后,這些農(nóng)軍戰(zhàn)士如何回鄉(xiāng)重樹義旗,組織暴動,最后隨朱德部隊參加湘南暴動,會師井岡山。
今天,讓我們來品讀《赤焰》第五章:飲馬長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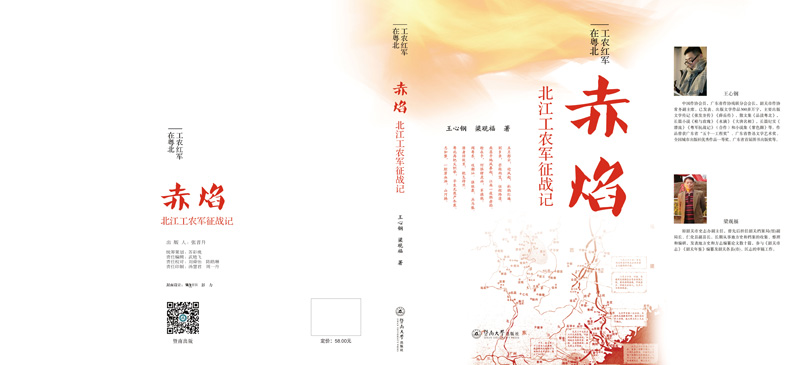
1
湖南永興,羅綺園一邊在督促樂民要做好留下人員思想工作,加強訓練,一邊在與武漢方面聯(lián)系,爭取部隊能早日北上武漢,以擺脫湖南反動軍隊的魔掌。
6月8日,被總部派去聯(lián)絡(luò)的朱云卿回到永興,說陳嘉祐已和三十五軍軍長何鍵溝通好,北江工農(nóng)軍可打著十三軍教導(dǎo)師補充團的番號,從永興出發(fā),先乘汽車到衡陽,再由衡陽搭船到株洲,后搭乘火車經(jīng)長沙到武漢。
羅綺園大喜,要求部隊迅速行動。陳嘉祐隨即命令沿線部隊,要確保補充團的安全,防止遭到長沙反對軍隊的襲擊。
雖是一路有許克祥部隊在虎視眈眈,但北江工農(nóng)軍官兵們?nèi)允桥d奮不已,畢竟好多人還是第一次坐汽車、輪船和火車,感覺十分新鮮和神速。6月15日,他們經(jīng)長途跋涉,安全到達武昌,被臨時安排在蛇山北面徐家棚的“春草堂”內(nèi)。
“春草堂”其實是一座花園,占地約有50多畝。園門前“春草堂”三個字據(jù)說是康有為的手跡。園內(nèi)亭臺、樓閣、小橋流水一應(yīng)俱全。花木茂盛。里面幾座平房正好做士兵營房。居住條件相當之好,只是沒有操場,練兵不方便,練兵時須到園外公路上,如遇上雨水,道路泥濘,顯得美中不足。
部隊到武漢后,羅綺園代表北江工農(nóng)軍,到國民黨中央農(nóng)民部匯報部隊由韶關(guān)到武漢的經(jīng)過。國民黨中央農(nóng)工部部長、中共黨員蘇兆征對該部不辭辛苦,千里迢迢來武漢參加革命的精神,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表揚。
6月20日,陽光明媚,部隊操練得不亦樂乎。中間休息時,參謀長朱云卿給戰(zhàn)士們動員鼓勁。“我們這支隊伍從韶關(guān)好不容易地來到了武漢,中間經(jīng)歷了千辛萬苦。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成為軍人,軍人,就應(yīng)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們現(xiàn)在做的事就是要好好練兵,練好一身本領(lǐng),將來上了戰(zhàn)場,就要真刀真槍地同敵人拼命。你們有沒有信心?”
“有信心!”戰(zhàn)士們響亮地回答。
周其鑒從外面進來,笑容滿面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今天下午,尊敬的何香凝女士會來探望我們。”
隊伍中,有知道何香凝這個名字的戰(zhàn)士一聽,立刻大聲叫好。
周其鑒繼續(xù)說:“何香凝女士是廖仲愷先生的遺孀,一直緊跟孫中山總理,是同盟會的老會員,國民黨的元老,她還是我們共產(chǎn)黨的好朋友。這次,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四·一二’政變,她公開反對蔣介石的暴行,與其決裂。她現(xiàn)任國民黨中央常務(wù)委員會候補委員,日理萬機,能抽出時間來探望我們,是對我們隊伍的關(guān)心。我們一定要用最好的訓練成績來報答何香凝女士!”
下午,陽光熾熱,何香凝在羅綺園的陪同下來到工農(nóng)軍駐地。何香凝舉止端莊,說話溫和,對來自廣東的工農(nóng)軍噓寒問暖,講了許多鼓勵的話。其中“誓不與民賊為伍,廣大革命黨員要團結(jié)起來打倒反革命派”的講話錚錚有力,給了官兵們莫大鼓舞。
何香凝離開駐地時,官兵們行軍禮相送,久久不愿放下舉著的手……
隨后,國民黨中央農(nóng)民部、中華總工會和武漢社會各界團體紛紛派代表來慰問看望,送來軍毯等慰問物質(zhì)。《漢口民國日報》先后以《粵中武裝農(nóng)工來鄂》等為題,報導(dǎo)了湖北總工會、婦女解放協(xié)會和漢陽各區(qū)農(nóng)會等團體慰問的消息,贊揚北江工農(nóng)軍“不失數(shù)千里山河跋涉的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實斟欽佩”。
6月29日,北江工農(nóng)軍指揮部派出林子光、侯鳳墀、梁功熾三個代表,前往中央農(nóng)民部,報告北江工農(nóng)軍的近況,對社會各界對該部的關(guān)心和慰問表示謝意,再次闡明北江工農(nóng)軍到武漢的目的,是在廣東軍閥壓迫下,“為著保存革命的實力,以圖拿紅色恐怖來打倒白色恐怖起見,所以克服艱難困苦而來革命的根據(jù)地武漢”,并表示今后“繼續(xù)努力,以求貫徹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初衷而酬雅望”。
2
作為北江工農(nóng)軍總指揮,羅綺園把隊伍安全帶到武漢后,心里落下一塊石頭。他此時更關(guān)心的是武漢急速變化的政治形勢。
蔣介石制造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武漢三鎮(zhèn)到處可見反蔣的標語,報紙上也每天登載反蔣的文章。革命陣營出現(xiàn)了大分化。南京方面不少反對蔣介石鎮(zhèn)壓工農(nóng)運動和不滿意其搞軍事獨裁的革命軍官,紛紛脫離蔣介石跑到武漢方面,有些受蔣介石排擠的部隊如第二軍、第六軍,也由南京轉(zhuǎn)到武漢方面。正是在這復(fù)雜背景下,第二次北伐誓師典禮在武漢南湖舉行。誓師大會后,張發(fā)奎便親率第四軍、十一軍從武漢出發(fā),于5月1日前全部開抵河南省駐馬店,集結(jié)待命。
接下來的戰(zhàn)斗是一場殘酷的惡戰(zhàn)。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北伐軍最后以付出了一萬余人傷亡的慘重代價,擊退了奉軍,把河南地盤無條件地交給了馮玉祥。然而,令北伐軍官兵們始料不及的是,馮玉祥卻是一個“騎墻派”,在他們前腳剛走,馬上表示不再支持武漢政府,倒向了蔣介石,而他們的初衷本是希望馮玉祥能與武漢政府合作,共同反蔣的。誰知竟成如此結(jié)局,白流了眾將士的血。
蘇兆征告訴羅琦園,“馬日事變”嚴重地摧殘了湖南的中共黨組織和工農(nóng)群眾團體。它給我們共產(chǎn)黨人提供了嚴重教訓,那就是不能滿足于表面上數(shù)字龐大卻沒有多少戰(zhàn)斗力的工農(nóng)武裝,必須有自己堅強的革命軍隊,同時實行攻勢的積極防御才是有效的,消極防守坐等人家來打,不預(yù)想反擊的措施只能是死路一條。
羅綺園問:“那么中央對我們廣東工農(nóng)軍有什么安排?”
蘇兆征沉默一會兒,說:“對于你們工農(nóng)軍到武漢的事,我在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政治局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上就提出過。為此,該委員會開會專門討論了相關(guān)議題。”說著,他掏出筆記本,讓羅綺園細閱相關(guān)的兩則會議記錄: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員會政治委員會
第廿九次會議速記錄(節(jié)選)
時間: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下午四時
地點:漢口中央黨部
出席者:林祖涵、陳公博、汪精衛(wèi)、孫科、吳玉章、陳友仁、譚延闿
主席:孫科
書記長:陳啟修
……
蘇兆征:廣東來的工農(nóng)自衛(wèi)軍如何安插?
譚延闿:最好是歸并第四軍,都是廣東人。
主席:請?zhí)K部長同張發(fā)奎軍長商量安插的辦法。
決議:照辦。
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
三十一次會議速記錄(節(jié)選)
時間:十六年六月廿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
地點:漢口中央黨部
出席者:孫科、林祖涵、陳友仁、王法勤、譚延闿、汪精衛(wèi)、陳公博、吳玉章、鄧演達
列席者:蘇兆征、詹大悲……
主席:汪精衛(wèi)
書記長:陳啟修
……
蘇兆征:處置廣東工農(nóng)自衛(wèi)軍的問題,已經(jīng)同張發(fā)奎、陳嘉祐兩同志接洽過,他們都愿意要,不過張同志要將他們補充各處缺額,陳同志答應(yīng)仍將他們編在一處,他們愿意到陳同志那里去。
主席:很好,就是這么辦,也不必作決議。
羅綺園對蘇兆征十分熟悉。他是廣東香山縣人,早年加入同盟會,參與領(lǐng)導(dǎo)了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和香港大罷工,歷任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共政治局常委、廣州蘇維埃政府主席和國民政府委員兼農(nóng)工部長,并在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后補委員。雖然每天忙得不可開交,但對工農(nóng)軍到武漢之事還是掛在心中。
蘇兆征說:“陳嘉祐率領(lǐng)教導(dǎo)師調(diào)移武漢后,武漢國民政府特將第二軍教導(dǎo)師、第五師和新成立三十九師合編成第十三軍,由陳嘉祐任軍長,下轄第五師、第三十八師和第三十九師,駐守湘南地區(qū),負責對廣東、貴州方向的警戒。你也看到了,在安置北江工農(nóng)軍時國民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有兩個意見,一是安排到張發(fā)奎的第四軍,二是安排到陳嘉祐的第十三軍。但張發(fā)奎提出將你們分散安排到部隊中以補充缺員,無形中打散了你們的建制;而陳嘉祐對你部十分熟悉,又是他把你們帶到武漢來的,因此,他同意保留你們原有建制,作為其屬下一個補充團,每月給你們6000元津貼費。”
“我部上下都愿意到陳嘉祐部,這樣才能確保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武裝不被打散。”羅綺園說。
蘇兆征說:“陳嘉祐已任命樂民為十三軍補充團團長。組織上決定任命你為國民政府農(nóng)工部秘書長,葉文龍則任中央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教育長。同時朱云卿,我們也將調(diào)他到武漢農(nóng)政訓練班工作,你看怎樣?”
“很好啊,我畢竟是個秀才嘛,不是帶兵的料。”羅綺園笑著說,“至于朱云卿是個未來的將才,更該重用才是。”
“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北江工農(nóng)軍雖然編入國軍序列,但實際上還是由我黨領(lǐng)導(dǎo)。中共中央和國民政府都清楚他們是工農(nóng)武裝,對他們相當關(guān)懷,決定發(fā)給部隊慰勞金一萬元中央紙幣,給每個戰(zhàn)士發(fā)兩套軍服。”
“太好了,官兵們一定會高興的。他們會服從黨的領(lǐng)導(dǎo),積極地完成上級交給的每一項任務(wù)!”羅綺園對工農(nóng)軍能“修成正果”,感到由衷的高興。
蘇兆征對羅綺園說:“你離開部隊前,要找樂民好好談一談,告訴他現(xiàn)在國共關(guān)系有走向分裂之勢。汪精衛(wèi)已有些動搖。唐生智已宣布擁汪反共,現(xiàn)在我黨可靠的部隊只有二十四師葉挺部,十一師周士第團和武漢警備團。張發(fā)奎或不反對我們,至于陳嘉祐,現(xiàn)時態(tài)度還好,不過他的部屬多是湖南人,將來恐怕不大可靠。工農(nóng)軍是本黨重要軍事力量,一定要掌握好。黨中央正設(shè)法將他們調(diào)入城內(nèi),隨時準備應(yīng)變。”
樂民當日即跑去武昌紙坊十三軍軍部面見陳嘉祐。
陳嘉祐見樂民到來,雖臉露笑容,但眉宇間顯有隱憂。“怎么樣?你部到武漢還習慣吧?”
樂民說:“部隊官兵情緒向來很好,日日都在抓緊訓練。日常訓練工作由副團長李資負責。駐地是一座大花園,環(huán)境優(yōu)美,可惜無操場可用。”
陳嘉祐聽罷,說:“現(xiàn)在國共兩方似不甚融洽,將來演變?nèi)绾危茈y逆料。不過你盡可放心,不論環(huán)境怎樣變化,我都要庇護你們,我絕不會做出對北江父老不住的事情,尤其是你本人,我對你倚望正殷,將來我必定設(shè)法提拔你。”
他點了支煙,又說:“昨日羅綺園同志來過,談及你們的駐地不便訓練的事,我已商得警衛(wèi)團方面的同意,將跑馬場的營地讓出給你們,此地與軍部較為接近,以后聯(lián)絡(luò)一切都便利得多。我已告訴沈參謀長,日間即有命令給你。”
“那真是太好了。”樂民知道陳軍長事多,起身告辭。
翌日8時起床,團部干部都來問樂民,外面的消息如何?他們看來極為關(guān)心時局的狀況。樂民告訴他們:“本團即將移駐武昌城內(nèi)跑馬場。”他們聽了大為雀躍。當天下午,果然傳到部隊移駐武昌城內(nèi)的命令。
部隊進駐武昌后,除了練兵之外,還注重加強政治和思想學習。朱云卿親自給他們上政治課,特地抽出一天時間,帶領(lǐng)大家到武昌起義始發(fā)處(中華民國政府鄂軍都督府)參觀,現(xiàn)場講述武昌起義的故事。
講到黎元洪當年操練新軍時,朱云卿語氣凝重起來。“黎元洪在操練新軍時,將新軍操練得很有成果。我想,我們北江工農(nóng)軍一定不會比黎元洪的新軍差,大家有沒有信心?”
戰(zhàn)士們齊聲高喊:“有信心!”
許多戰(zhàn)士站在莊嚴的都督府面前不禁浮想聯(lián)翩,想起在家鄉(xiāng)鬧革命時的情景,那是多么地痛快淋漓。而現(xiàn)在遠離故鄉(xiāng),穿上軍裝肩負重任,其中不僅有親人重托,更有自己的信仰。
軍人,就是為戰(zhàn)爭而生,為和平而生。“秦時明月漢時關(guān),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唐朝詩人王昌齡的名句,正體現(xiàn)了戰(zhàn)士們此刻心情。
3
夏季的武漢熱得像只大火爐,烤得人不動也在不斷冒汗。市民們晚上都不呆在房里,男女老少一人一張涼床,全都跑到露天里睡覺。而從廣東來的工農(nóng)團戰(zhàn)士更受不了這悶熱蒸烤,恨不得整天泡在水里才好。
此時,比天氣更悶熱的是武漢的政治。6月5日,共產(chǎn)國際代表羅易把共產(chǎn)國際的5月緊急指示送給汪精衛(wèi)看,幻想爭取汪精衛(wèi)的同意。汪看后暫時沒有表態(tài),但已種下了與共產(chǎn)黨分道揚鑣的種子。6月27日,武漢國民政府應(yīng)馮玉祥的要求,決定解散工人糾察隊,逼迫共產(chǎn)黨人譚平山、蘇兆征辭去所任國民政府部長的職務(wù)。
7月的武漢大雨連綿,新的洪峰在長江上游醞釀。中共中央是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進行了改組,由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zhí)缀蛷垏鵂c五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履行中央政治局職權(quán),陳獨秀停職。鑒于汪精衛(wèi)集團已在公開地準備發(fā)動政變,中共中央于7月13日發(fā)表《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罪行,宣布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chǎn)黨員,并莊嚴聲明,中國共產(chǎn)黨將繼續(xù)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愿意同國民黨的革命分子繼續(xù)合作。
7月14日晚,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召開秘密會議,接受了汪精衛(wèi)提出的“分共”主張。15日,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舉行第二屆常務(wù)委員會第二十次擴大會議。汪精衛(wèi)在會上宣讀了“共產(chǎn)國際五月指示”,并就其內(nèi)容發(fā)表了長篇講話,決定與共產(chǎn)黨正式分裂。
7月24日,中共中央發(fā)表《對于武漢反動時局之通告》和《致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書》,強烈抗議武漢國民黨中央作出的"分共"決定,號召革命的國民黨員應(yīng)與叛變革命的汪精衛(wèi)集團決裂,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革命政綱和三大政策,明確表示中國共產(chǎn)黨員決心和革命的國民黨員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繼續(xù)孫中山的國民革命事業(yè)。
“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后,大革命宣告失敗。國民黨多次反革命政變的事實,打破了北江工農(nóng)軍原來所懷的美好革命理想。全團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甚至有點人心惶惶。有些干部甚至脫離工農(nóng)軍,投奔到張發(fā)奎的部隊中去。
剎那間,呈現(xiàn)出一派“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的困境。
其時,陳嘉祐忽然下令,十三軍補充團長樂民改任團政治指導(dǎo)員,另派參謀長沈鳳威兼任團長一職。
在這種情況下更換軍事主官,引起官兵們許多猜測。周其鑒就表明反感的態(tài)度,因為沈鳳威曾在北江鎮(zhèn)壓過農(nóng)運,是個臭名昭著的反動軍官。好在沈鳳威心不在此,來了不幾天又調(diào)離補充團,仍由樂民以政治指導(dǎo)員兼代團長,主持全面工作。官兵情緒才稍微安定下來。
7月21日,周其鑒和樂民接到中共中央密令,要他們迅速脫離陳嘉祐十三軍,將隊伍開赴南昌集中。
他們當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決定將在南昌進行武裝起義,只是認為寧漢合流之后,中共采取的一種行動。不過,他們也從其他渠道得到“共產(chǎn)黨及一切革命分子與賀龍,葉挺軍隊在南昌另組革命委員會。提兵南下廣東,討伐李、黃、錢、鄧諸逆,實行土地革命、解放農(nóng)民,建立工農(nóng)革命政權(quán)與南京政府對抗”的消息。
然而要離開武漢去南昌,并非易事。作為團主要負責人,樂民不得不做鄭重考慮。一方面,北江工農(nóng)軍是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武裝,不能不服從上級命令。另一方面,該部又同時屬于第十三軍補充團,如果不遵守軍令而擅自行動,會被以叛軍罪論罪,要遭到軍法和嚴厲處分。更何況武漢近郊駐扎眾多國民黨部隊,北江工農(nóng)軍紅色標志明顯,若是私自離開部隊,給其他部隊發(fā)覺,必定會被追擊。以北江工農(nóng)軍區(qū)區(qū)600余人,經(jīng)不了人家?guī)紫麓颍芸炀蜁弧鞍孙溩印薄?/p>
樂民想來想去,想出一個自認為較好的理由。他親自登門找軍長陳嘉祐協(xié)商,說土兵們因在武漢水土不服,導(dǎo)致不少人患病,加之農(nóng)民觀念太重,離鄉(xiāng)日久而生思鄉(xiāng)之情,一個個都在鬧情緒想回家。能否請陳軍長恩準,同意北江工農(nóng)軍離開武漢回廣東家鄉(xiāng)?
陳嘉祐一聽有些意外,他與北江工農(nóng)軍關(guān)系很深,感情融洽,知道該團官兵都很年輕,基本上是二十歲左右青年人,大部分有文化,革命情緒很高,懂紀律,比一般軍隊官兵素質(zhì)強許多。當前正是擴軍用人之際,哪里舍得讓他們走?
陳嘉祐說:“別輕意說走嗎,有什么事不能解決?我去做做他們的思想工作。”
果然,陳嘉祐以軍長身份親自到部隊駐地,給全體官兵訓了兩次話,希望官兵們繼續(xù)留在十三軍,為完成北伐的使命而共同奮斗。陳嘉祐訓話時,言詞懇切,講到激動之時,不禁聲淚俱下。官兵們也深受感動。
周其鑒在一旁聽著,感慨萬端。北江工農(nóng)軍自5月初追隨陳嘉祐教導(dǎo)師入湘,雖只有兩個多月,但得陳嘉祐幫助不少,由于他駐韶關(guān)有年,對工農(nóng)運動素來熱心和關(guān)注,與北江革命同志合作得非常緊密。入湘后,工農(nóng)軍常得到他的照顧,駐地必選擇最安全的地方。部隊經(jīng)過長沙時,他亦派軍掩護,確保萬無一失。到達武漢后,官兵們都希望能繼續(xù)追隨于他,為革命事業(yè)而努力。可是誰也沒有想到,時局變化出乎人意料之外。彼此之間雖有不舍,但又必須分離。畢竟,陳嘉祐部從屬于日益走向反共的唐生智集團,而工農(nóng)軍是共產(chǎn)黨的部隊,必須服從黨的指揮。此時擺在工農(nóng)軍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生路,一條是死路。革命就是生路,不革命就是死路。所以只能心底里對陳軍長說一聲對不住了。
陳嘉祐見工農(nóng)軍去意已決,知道再挽留也無濟于事,畢竟這是一支以中共為主的隊伍,形勢不允許。他也不想同中共發(fā)生沖突。他同中共領(lǐng)導(dǎo)有很深的交往,知道工農(nóng)軍說水土不服要回廣東只是一個借口,其中肯定有更重要的原因。他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只好答應(yīng)好聚好散,絕不會干涉工農(nóng)軍的自由,何去何從由大家自己決定。
樂民見陳嘉祐同意后,便命令部隊趕快做好準備,以最快速度離開武漢,開赴南昌。臨行前,他交代,全軍在脫離第十三軍時,要將陳嘉祐當初撥給的槍械全部退還,好讓陳軍長有個交待,也不至于讓那些對他有成見的人抓住把柄。
這個命令讓好些工農(nóng)軍戰(zhàn)士想不通。歐日章就跳出來反對。“我們曲江農(nóng)軍的槍都是從敵人那里繳獲的,沒有槍還算什么軍隊?不如回家當農(nóng)民算了。”
周其鑒出來做工作:“我們表面上說是回廣東,600多人帶著槍走目標太大,弄不好會被其他軍隊連人帶槍一窩端了去。更何況到了南昌回到自己人的部隊,何患無槍?”
這一解說,官兵們漸漸明白過來,默默把心愛的槍再擦拭一遍,依依不舍地交了上去。
陳嘉祐對工農(nóng)軍這個義舉感到欣慰,密令部隊放行,確保補充團秘密撤離武漢。
陳嘉祐后來一直不愿意和蔣介石合作,被蔣介石視為眼中釘,迫其居地常遷。1935年陳嘉祐遷居香港,兩年后病逝,終年56歲。后妻兒遵囑,將其安葬湘陰南泉寺。這是插話。
7月29日一早,600多名北江工農(nóng)軍官兵從武漢分乘三艘小火輪由長江順水東下。碼頭上擠滿張發(fā)奎準備東征的部隊。
時值夏秋之初,水流湍漲,兩岸青山不斷朝后飛去。官兵們心情激動,無暇顧及秀麗景色,恨不得一下子就到達目的地。黃昏時分,部隊安全到達江西九江,并在市區(qū)宿營。這里是張發(fā)奎東征大本營,布防嚴密,不能久留。
第二天一早,北江工農(nóng)軍轉(zhuǎn)乘火車到達南昌,一下火車,就有人員前來聯(lián)絡(luò),隨即編入葉挺第二十四師教導(dǎo)團(即七十二團)駐扎在新營房。隨隊伍到達南昌的工農(nóng)軍負責人有,卓慶堅、周其鑒、樂民、李資、甄博雅、宋華、盧克平、林子光和李甫等人。
隊伍剛一駐扎下來,葉挺就派人前來慰問。葉挺是北伐名將,工農(nóng)軍官兵早有耳聞,對其相當佩服,現(xiàn)在能編入葉挺鐵軍中,心情更為激動,一個個摩拳擦掌,準備迎接新的戰(zhàn)斗。
只是沒想到,他們即將參加的是一場名垂青史的南昌暴動。


掃一掃,關(guān)注廣東殘聯(lián)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