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我們將迎來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為了以文學的形式生動反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取得民族獨立與解放的光輝歷程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用優秀的文學作品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即日起,廣東省殘聯將于官方網站“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專題的“自強與助殘”欄目定期每日更新由中國作協會員、廣東省作協殘聯分會會長、韶關市作協常務副主席王心鋼主創作的“粵北紅色三部曲”——反映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廣東省委和南方工委在粵北的長篇紀實《潛流》、反映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鋒面雨》和反映大革命時期北江農民運動的《赤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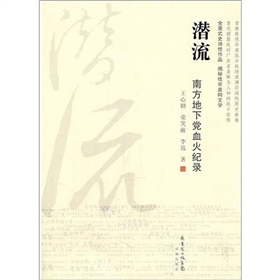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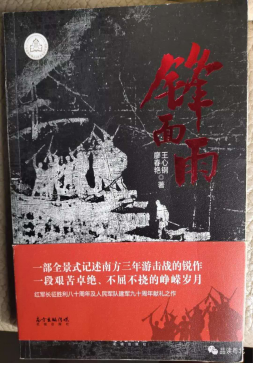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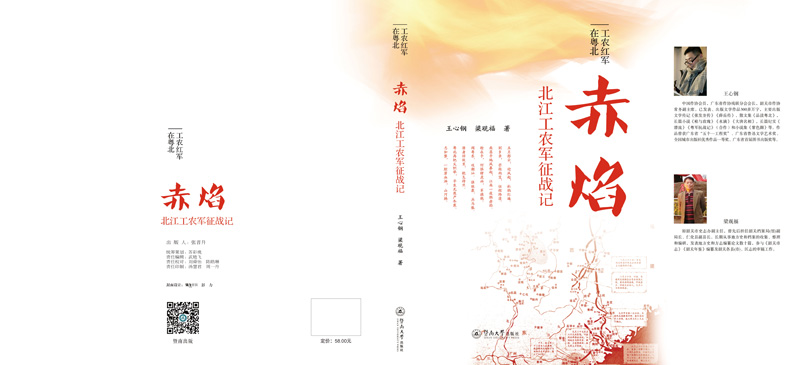
?
長篇紀實《潛流》由廣東省作協殘聯分會會長王心鋼、韶關市作協主席榮笑雨和國家二級作家李迅共同創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華南抗日戰場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詩性作品,涉及的歷史事件主要有廣州淪陷、韶關成為戰時省會,兩次粵北會戰,香港營救文化人、東縱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點塑造了紅色省委書記張文彬烈士的光輝形象,人物有血有肉,豐滿可信。作品基于革命現實主義之上的傳奇想象,富有情節性、故事性、傳奇性、可讀性。通過此書,讀者將真實了解到抗戰時廣東省委的烽火歷程,感受一代共產黨人為了民族解放的獻身精神。
今天,讓我們來品讀《潛流》序章:洛川點將。
1
雷雨過后,西天燃起一大團一大團的火燒云,映紅了巖崖,映紅了洛水,映紅了窯洞前剛掛果的棗樹。毛澤東夾著煙卷從窯洞里出來,站在院子里,仰看變幻莫測的紅霞,若有所思。
位于延安南部的洛川縣,是一個古老的小縣,因境內洛水而得名。三國時的曹植在其《洛神賦》中唱曰:“容與乎陽林,流沔乎洛川。”此洛川即為洛水。洛川境內,到處可見獨特奇異的“黃土喀斯特”地貌景觀,土塬裸露,黃壁直立,谷坡陡峻,在火燒云的輝映下更顯得鬼斧神工、氣勢恢宏。
離洛川縣城北10公里,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村莊叫馮家村,因中央紅軍的到來,這里成為紅軍最高指揮部駐地。1937年8月22日,村前村后,山崗上下,布了雙崗,顯然有一個重要會議在此召開。如果有記者到那簡樸的會場采訪的話,會大吃一驚,因為與會者大都是中共大腕級人物,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有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任弼時、關向應、凱豐、彭德懷、張國燾;紅軍高級將領及有關方面負責人有劉伯承、賀龍、張浩、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張文彬、肖勁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鐘等,共22人。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共開了四天,作出許多重要決定,史稱“洛川會議”。
毛澤東在窯洞前來回踱了很久,直到火燒云完全消失天空已是鐵藍的一片,似乎也沒拿定主意。他回頭對身邊走過的勤務兵說了句:“小鬼,去把恩來同志請來。”
“是。”勤務兵應了一聲,一溜煙不見了。
不一會兒,周恩來笑吟吟地走進院子:“主席,這種時候不是邀請我數星星吧?”
“不數星星,數人。”
“數人?”
毛澤東作了個請的手勢,請周恩來在一個石桌前坐下:“恩來,時間不等人了,再看看幾個你想要的人。”
周恩來拿起石桌上的紙條,上面用鉛筆寫了三個人名,紙條是周恩來寫的。“主席想好了嗎?”
“廣東,不能再這樣冷清下去了。”
“我們在那里的工作一直不順利。是要有個能干的人去。”
“盧溝橋事件爆發后,國共兩黨的爭論已不是應否抗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是實行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反對片面抗戰路線。”毛澤東吐了一口煙道,“這次洛川會議,我們達成了共識,中國的抗戰是艱苦的持久作戰,必須經過持久作戰,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會議的核心就是要避敵鋒芒,開拓敵后游擊區,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要把黨的工作重心放在戰區和敵后,迅速開辟廣東的根據地非常必要。”
周恩來心里清楚,廣東是辛亥革命的發源地之一,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搖籃。1926年,在國共精誠合作下,不僅在廣州建立了黃埔軍校,而且取得了東征、北伐的勝利。然而“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后,廣東卻成為工作開展的重災區。由于國民黨的殘酷鎮壓和叛徒的出賣,中共廣東省委曾遭受三次嚴重的破壞,至1934年3月,中共在白區的有組織的活動基本中斷,幸存的黨員轉入隱蔽狀態,數量也不斷減少。現在國共提出第二次合作,正是重新打開廣東局面的大好時候。
“主席說得對,我們就是要全面開花,在全國建立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
“這幾個人里,誰去最合適?”
“中間那個。”
“理由?”
“主席不是已經考慮好了嗎?”
“怎么講?”
“在中間的名字下面還劃了一道杠。”
“一筆露天機呀,你看怎么樣?”
“就他,沒人比他更好了。文韜武略,大將之才。”
“恩來,你是不是早有預謀了?要不你也不會把他的名字寫得最大。”
“這么說我也是有意為之嘍?哈哈,瞞不過你呀……只是,身邊的得意門生,主席舍得讓他離那么遠?”
“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志嘛。”毛澤東說著,把兩邊的兩個名字劃掉,留下了中間的一個名字。
中間的這個名字是:張文彬。
“去把文彬同志請來吧。”毛澤東叮囑了勤務兵一句。
“是。”勤務兵一個轉身又不見了。
2
村口,一場籃球賽剛剛結束,勤務兵一眼就看見長得又瘦又高的張文彬,“啪”地敬了個禮:“主席有請。”
張文彬有一米七六的個子,愛笑愛鬧,性格活潑,爽朗隨和,辦事干脆利落,判斷力強。他用毛巾擦了把汗,忙穿起軍服,邁開長腿便往主席的窯洞跑去。
張文彬,原名張莼清,l910年7月5日(農歷五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在家排行最小,上有兩個哥哥和兩個姐姐。1923年,他小學畢業后,得其堂兄張子謀資助,到長沙中學讀初中。
1926年11月,張文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4月,黨組織選派他到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成為毛澤東的學生。6月,受訓結業后他回到平江家鄉。這時,“馬日事變”已經發生,許克祥在長沙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到處白色恐怖。張文彬參加了中共平江縣委領導的平江秋收暴動,高唱著“梭鏢亮光光,擒賊先擒王。打倒蔣介石,活捉許克祥”的戰歌,先后于8月、10月兩次參加攻打平江縣城的戰斗,后因敵我力量懸殊和經驗不足遭到失敗。
1928年7月22日,張文彬參加了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等領導的平江起義,并任紅五軍第一營黨代表,成為彭德懷手下的一員猛將。1929年,19歲的張文彬擔任紅三軍團紅五軍政委,后又任紅七軍政委、紅三軍團保衛局局長。1934年10月,張文彬隨中共中央和紅軍主力參加長征,次年10月到達陜北后,任紅十五軍團東渡黃河司令部政委。
1936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從紅軍中抽調一批高中級干部到瓦窯堡成立紅軍大學,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統一戰線政策和戰略戰術,毛澤東任校務委員會主席,并親自授課,林彪為校長,張文彬奉調參加學習。紅大學生按職務和有關條件分編成一、二、三科,張文彬被分配到由師團級以上干部組成的第一科。
張文彬原以為可在紅軍大學好好地學習一段時間,沒想到學習不滿三個月,便接到新任務。他猶記得8月13日那個黃昏,在瓦窯堡紅軍大學普通窯洞里,外面風雨大作,窯洞內卻談笑風生。一個特別的晚宴正在舉行。
當天早上,學校接到中央的通知,將派一批得力的干部到國民黨軍隊做統戰工作,其中,派張文彬到西安做楊虎城的統戰工作,張經武(長征時曾任軍委縱隊參謀長,到陜北后任軍委二科科長)到山東做韓復榘的統戰工作,另外,調童小鵬接任毛澤東的秘書。張文彬、張經武和童小鵬三人都是紅軍大學一科同學,又是同一天調出,意義非常。紅軍大學教育長羅瑞卿特地在保衛局食堂加了幾個菜,為他們餞別。菜不多,氣氛特別地熱烈,大家海闊天空地聊著,興致起來,不禁又唱又跳。
童小鵬敲了一下盆子提議說:“哎,各位靜一靜。文彬平時喜歡吟幾句詩,大家叫他‘詩人’,經武在白區工作過,愛講幾句生意經,大家叫他‘老板’。今天我們為‘兩張’送行,似乎應該作詩送別才是。我提議,請詩人來一首。”
在座的鼓掌敲盤,表示贊成。
張文彬站起來,笑著說:“平時都是我一個人作詩,今天換個形式,一人一句,怎么樣?”
張經武大爽快地說:“行,你來第一句。”
張文彬望著風雨大作的窗外,隨口吟道:“狂風暴雨宴經武。”
張經武哈哈大笑,道:“好,我跟一句:且談且笑送詩人。”
童小鵬見桌上只有一瓶從西安搞來的葡萄露,便靈機一動,舉起酒杯高歌:“葡萄美露聊當酒。”
羅瑞卿摸了摸胡子,充滿期待地望著三位得意門生,續上最后一句:“翹首秦中報捷音。”
大家連聲叫好。
第二天一早,在中央保衛局接受任務后,張文彬便帶著報務員、交通員和電臺上路了。他們經十七路軍與瓦窯堡之間的秘密通道抵達西安,秘密進入軍營,見到了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將軍。
楊虎城展開張文彬遞上來的介紹信,上面赫然蓋著毛澤東的簽名章:
楊虎城先生勛鑒:
日寇進攻,國家危急,亟宜一致奮起,組成堅固的抗日陣線,為著堅決保衛平津,保衛冀、察、晉、綏、山東,與仇敵血戰到底之總方針而斗爭,弟等對楊虎城先生抗日決心甚為欽佩,茲派張文彬同志前來晉謁,請予接洽交換意見,并賜指示,以期驅除強敵共救危亡。
臨書不勝屏營系念之至,敬致抗日民族戰爭之敬禮!
毛澤東(蓋章)
楊虎城大喜,特地囑咐其憲兵營對張文彬這位中共密使,實施嚴密保護。
在西安,張文彬先后與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楊虎城本人多次進行商談,最終促成了中共同楊虎城領導的十七路軍達成三項協議。此后,中共在楊虎城部隊里建立了“紅軍秘密聯絡站”,張文彬作為紅軍駐十七路軍代表暫住西安,其公開職務是十七路軍總部政治處主任秘書,但實際上還擔負著領導中共西北特別支部的工作。
同年12月上旬,驚聞張學良、楊虎城與中共秘密合作,蔣介石從南京飛到西安,住進了臨潼清華池。張文彬與中共地下黨組織精心部署了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的萬人游行活動,以此為契機引發各界民眾對蔣介石反共賣國政策的抗議。國民黨西安當局出動警察驅趕游行隊伍,打傷數十名學生,張文彬抓住機會組織更多的群眾赴臨潼向蔣介石請愿。這次請愿行動規模空前,民眾情緒悲憤,秩序良好,對其后不久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捉蔣行動起到了直接的促進作用。
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派出了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介入事變的調解談判,張文彬是代表團成員之一。由于有張文彬等提供的第一手資料,代表團對事變的全過程有著具體翔實的了解,對于迅速地確定釋蔣的決策打下基礎,有力促進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隨后,黨中央派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和張文彬四人為中共代表同國民黨談判,張文彬并被任命為紅軍駐蘭州辦事處主任。
1937年春,紅軍西路軍在無根據地和后勤保障的條件下,孤軍深入,幾經浴血奮戰,在敵強我弱、寡不敵眾的情況下,兩萬余官兵被俘的被俘,失散的失散,還有不少年輕的生命葬身大漠草原和馬家軍騎兵的屠刀之下。中共中央十分關心西路軍官兵的安危。2月,電示周恩來和葉劍英要千方百計設法營救他們。
葉劍英長征時曾在紅四方面軍工作過,接到中央指示后,心中十分焦急。由于正在參加國共談判,他和周恩來商量后,將這項工作交給張文彬負責,并一起研究了營救方案,決定一方面設法到回民中間摸清情況,看有多少人散落在群眾之中;一方面托關系與青海、甘肅當局上層交涉,要他們交還被俘人員。周恩來特地交代張文彬,要重點營救被包圍在黃番寺500余名紅軍指戰員,只要馬家軍隊不傷害被圍紅軍,可以交槍和平解決。
張文彬通過著名民主人士杜丞斌先生和從事地下工作的吳鴻賓,很快在西安回民中物色到一位和馬家軍有聯系的人。此人叫馬德涵,曾在甘肅教書,為人正直,政治上可以信賴,且與馬麟熟識,與馬步青有師生之誼。馬德涵先生獲悉是周恩來先生所托后,當即慨然應諾。
同年2月底,張文彬陪著馬德涵乘飛機從西安抵達蘭州,隨即又轉乘汽車來到武威,見到了西北王“二馬”之一的哥哥馬步青。
張文彬坦率地與馬步青研究西路軍的改編和生活問題,目的是不讓殺害紅軍,生活上給予照顧。馬步青迫于形勢,答應可以解決,并口頭表示將如數釋放被俘紅軍,愿將自己改編紅軍組建的工兵團和童子軍遣送西安。
隨后,張文彬帶著馬步青給弟弟馬步芳的親筆介紹信,只身來到青海西寧,見到了馬步芳。雖然,馬步芳對共產黨仍有戒心,但也口頭擁護西安事變國共抗日的政治綱領和主張。征得馬步芳的同意,張文彬正式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甘肅馬家軍一個集中營看望被俘紅軍戰友。
黃沙飛舞,長煙落日。望著骨瘦如柴、胡子拉碴的戰友們,張文彬不禁熱淚盈眶。而紅軍戰俘們自被捕后第一次看見黨中央派來的親人,更是格外激動,不禁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紅軍萬歲!”
張文彬從青海回來后,到延安向周恩來和葉劍英作了匯報,說經過實地調查發現,被俘官兵普遍受到人身虐待,有的已慘遭殺害。葉劍英立即以中共代表身份會見西北行營主任顧祝同,要求馬家軍交回紅軍被俘人員。顧祝同答應予以合作。
正當張文彬積極參與營救紅軍戰俘行動時,中共中央書記處發來通知,讓張文彬到洛川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他便預感到又有新的任務。
3
“報告。”張文彬給毛澤東、周恩來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后,急切地說:“兩位首長,會議結束了,是不是有新任務,派我上抗日前線去?晉察冀還是華東?”
毛澤東寬厚地笑著說:“你這個伢子,蠻有腦子的,再往遠處想一下……哎,莫急莫急,事情要做,飯也要吃,你我今天不談工作的事。今天我是請你來吃爆炒辣椒和紅燒肉的。”
張文彬在毛澤東身邊擔任過政治秘書,知道毛澤東好這口,聽說有肉吃,他高興得把袖子一挽:“好久沒吃紅燒肉了,今天‘打牙祭’,我去幫廚。”
毛澤東打心里喜歡湖南小老鄉,他沖張文彬擺擺手:“坐下,今天老鄉請老鄉,你是君子,動口不動手,我們兩個好好聊下子天。如果要任務的話,你找恩來同志要去吧。”
周恩來接了一句:“難得主席今天心情好,咱們邊陪主席吃紅燒肉邊聊天,任務的事吃飽肚子再說。”
“好的。”張文彬嘴里應著,轉身跑到廚房幫上菜。
飯菜上桌,三人先從眼前的紅燒肉聊到長沙臭豆腐,再從廣州農運講習所聊到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繼而聊到遵義會議、西安事變,直到剛結束的洛川會議。聊著聊著,自然切到了張文彬這次南下的新任務。
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為統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發展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運動,中共中央計劃在武漢設立中共中央長江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長江局負責管轄云南、貴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省,并領導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新四軍的工作。為籌建長江局,周恩來在諸多紅軍將領中物色著合適的才干。他慧眼識珠,看中了張文彬。
周恩來對張文彬的真正了解,是在西安事變的那段日子。他看出了張文彬在黨內青年干部中是個難得的人才,他年輕有為,斗爭堅決,好學上進,既有豐富的軍事知識和戰斗經歷,又有從事組織建設和統戰工作的實際經驗,真可謂才華橫溢,文武雙全。
周恩來親切地對張文彬說:“文彬同志,中央決定,你要脫下軍裝,到廣東去開展工作,整頓和加強廣東黨組織,領導華南抗日救亡運動。”
毛澤東一旁意味深長地說:“東坡先生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你要在蔣介石統治下的國統區工作,很不容易,你到廣東要依靠黨,要廣泛依靠群眾,建立統一戰線,扎下根子,不妨長作‘嶺南人’吧。”
張文彬原以為會派自己回部隊上抗日前線指揮戰斗,沒想到是派自己到廣東做地方黨工作,有點愕然,但很快明白了兩位領導人在廣東布局的重要意義,爽快接受任務。
談到興處,周恩來拿起茶杯,從文件包里變戲法一樣拿出一瓶邊區老燒。“來,借主席的一道美味,紅燒肉,一杯淡酒,算是餞行。下一杯,主席,我想是不是應該在廣東喝了。”
毛澤東笑而不語,張文彬馬上醒悟:這是在等自己表態呢。他起身端起酒杯,“那我就帶上主席愛吃的辣椒,把廣東這桌粵菜燒好,為主席和周副主席接風。”
毛澤東大笑:“哈哈,好一個湘風南漸,這句話我愛聽。”
在洛川這么久,張文彬第一次看見毛澤東如此開懷大笑。
用完晚飯,離開毛澤東窯洞,周恩來和張文彬踏著淺白的月光向村后的土崗走去。張文彬一直不語,左手提著風燈的周恩來也配合著這種沉默,他知道張文彬在想什么,他打算讓張文彬想透了再說。
走出半里路,張文彬緊走幾步攔住周恩來。周恩來一笑。“哈,張文彬同志憋不住了吧?是不是有點意外?”
“只是……周副主席,你說,我能做好廣東的工作嗎?那可是國民黨的老巢。”
“你不要忘記了,那也是中國革命的策源地,辛亥革命,北伐,農民運動講習所。”
“這個我當然明白。”
周恩來頓了一下,告訴張文彬:“中央派你到廣東,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他來處理好中共廣東黨組織內部存在已久的黨內矛盾,即‘南、市委糾紛’問題。”
原來,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分別派遣薛尚實、王均予開展華南和廣東地區的工作,恢復和重建黨組織。同年9月,由薛尚實報請北方局批準,在香港成立了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負責廣東、廣西、云南、貴州等地工作。而王均予則在廣州發展黨員,建立基層黨組織,并于同年12月籌建了中共廣州市委。所謂“南、市委糾紛”,開始是中共南方工委書記薛尚實和廣州市委書記王均予兩人之間在工作上產生的意見分歧。客觀上是由于在地下斗爭特殊環境中彼此難于溝通,主觀上則是由于薛、王二人未能正確處理黨內矛盾,彼此不買對方賬,致使意見分歧,發展成為政治上的互不信任。
1937年5月,中央在延安召開白區工作會議期間,中央領導同志張聞天、博古就曾單獨接見廣東代表王均予(另一代表薛尚實未赴會),在詳細聽取了廣東黨組織情況匯報后,對“南、市委糾紛”問題表示關注。會議結束后,張聞天寫了親筆信給王均予帶回(此信后轉交薛尚實),信內囑咐廣東同志搞好團結。但張聞天的親筆信未能使“南、市委糾紛”得到解決。不久,南委向中央提出報告,要求調離王均予和改組廣州市委,中央未予答復。在此前后,南委著手在廣州組織工作團,意圖以此工作團取代原有的廣州市委。南委派人正式通知廣州市委,宣布撤消廣州市委書記王均予的工作,解散廣州市委。這一決定導致南委和廣州市委之間的組織對抗,成為南、市委糾紛尖銳化的焦點。廣州市委拒絕接受南委的處分,南委組織的工作團則在廣州開始進行活動,廣州出現了兩個互不協調的中共組織同時存在的局面。為此,王均予親自從廣州跑到延安,要求中央派得力的干部來廣東,徹底解決“南、市委糾紛”。
張文彬聽完情況介紹,皺了皺眉頭:“怎么會這樣,這不是在拿黨的事業開玩笑?王均予現在在延安嗎?他跟我一起回廣州?”
“不,他說有薛在就不回去,愿意留在延安。”周恩來站在崗頂上,望著彎彎的下弦月,解釋說,“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要重振廣東這塊革命策源地的雄風,需要在南方樹起一面與陜甘寧根據地遙相呼應的旗幟。所以對你來說,是天降大任與斯人了。”
“我擔心的就是這個,沒有南方工作的經驗,人際關系陌生,會不會水土不服啊?”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個偏方治一種病。水土不服?有藥可治的嘛,別以為就你一個人孤軍獨斗。告訴你吧,這次回廣東,不單是你一人,中央軍委將派張云逸、廖承志、云廣英等以中共代表的公開身份到廣州、香港組建八路軍辦事處。在閩粵邊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方方也來到延安,重新與中央取得聯系。你到廣東后,要好好和他們幾人合作,開創新局面。”
“真的?那太好了。”張文彬聽了充滿信心,并問,“我是否和方方同志同行?”
“原本安排你倆同行的,但方方接到改編南方游擊隊的任務,已提前走了。”周恩來望了望,見四下無人,便從內衣口袋掏出一張小紙條,低聲說,“你這次到廣東從事地下工作,身份是秘密的,廣東的政治形勢復雜,還存在很大的危險,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我派一名代號‘03’的同志暗中護送你南下。‘03’平時不和你見面,只在緊急情況下與你聯絡。這是聯絡暗號,你記住。”
“是。”張文彬強記住暗號后,便把紙條揉成一團,咽進嘴里,并淺笑著說,“難怪副主席姓周。”
“嗯?這話什么意思?”
“考慮周密嘛。”
“哈哈哈,夸我還要繞圈子……總之,廣東的這桌菜怎么做就看你文彬老弟了,剛才你說了,要做好這桌粵菜的,我和主席都等著。”
“粵菜,辣椒,哼哼,辣椒,粵菜。”張文彬像在接周恩來的話,又像在自言自語。
周恩來把風燈往高處舉舉,照著張文彬的臉,問:“你想說什么?”
“想說的很多,一時又無從說起。”
“能理解。心緒浩茫似無邊,一旦到了那里你自然就頭緒清楚了,什么時候有想法都可以直接跟我說。”
“不說了。”張文彬“咔”地雙腳一并,鄭重其事地行了個軍禮。
周恩來微笑道:“好,行動永遠比語言有力,那我把你的這個軍禮理解為承諾了。一個莊重的承諾。”說完把右手伸向張文彬。
張文彬握住周恩來的手,突然醒悟道:“你看我,周副主席,應該我來提燈才對的。光想著我自己的事了。”
“這話說反了,文彬同志,今天是我送你,也代表主席送你,我來提燈才是對的。主人照路客人行嘛……當然你也不是客人,而是一個遠行人。”
夏夜的風吹來,把張文彬亢奮的心吹得呼啦呼啦的。
9月上旬,張文彬按照中央保衛局安排的路線,自延安南下,輾轉西安、武漢、上海,抵達香港,再從水路秘密進入廣州,與當地黨組織取得聯系。
臨行前,他向毛澤東辭別,并請示主席還有什么指示沒有?毛澤東深思片刻,伏案執筆,抄了一篇舊作《清平樂·會昌》給張文彬: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


掃一掃,關注廣東殘聯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