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紀實《潛流》由廣東省作協殘聯分會會長王心鋼、韶關市作協主席榮笑雨和國家二級作家李迅共同創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華南抗日戰場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詩性作品,涉及的歷史事件主要有廣州淪陷、韶關成為戰時省會,兩次粵北會戰,香港營救文化人、東縱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點塑造了紅色省委書記張文彬烈士的光輝形象,人物有血有肉,豐滿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現實主義之上的傳奇想象,富有情節性、故事性、傳奇性、可讀性。通過此書,讀者將真實了解到抗戰時廣東省委的烽火歷程,感受一代共產黨人為了民族解放的獻身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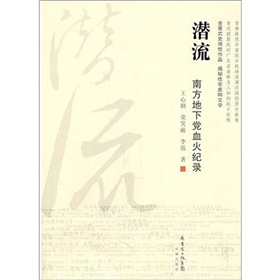
今天,讓我們來品讀《潛流》第十七章:姐妹鋤奸。
1
韓江像一條銀練橫貫于粵東大地。正值汛期,夏雨滂沱,洪水猛漲,沿岸低洼處的農田、茅舍幾被淹沒,渾黃的河水夾著流柴枯草打著漩渦直卷而來,甚是兇猛。碼頭上沒有大而醒目的建筑物,低矮的泥磚小瓦房散落于環形半島。粉面店、小飯館、涼茶攤和幾間小商鋪排列在沿江的河街上,小販時高時低的吆喝聲,給冷清的碼頭帶來一絲兒生氣。靠碼頭的河面上,停泊著十幾條漁船,有的在淘米做飯,有的在裝卸貨物,有的在修補船網,不遠處,一個四十開外的漁夫跳下船,赤裸著古銅色的身子,把兩大筐裝滿仍在蹦跳的魚兒擱在岸邊,用一條大竹杠挑起,大腳“吧噠吧噠”地踩在青石板上,嘴里發出“吭唷吭唷”的聲音。
此時,從河上游“突突突”地駛來一艘機帆船,船頭站著兩名戴大蓋帽、穿黑制服的水上警察,大聲吆喝著,要漁船讓路。機帆船剛一靠岸,碼頭上一陣人聲騷動,接著傳來汽車的引擎聲,一輛美式軍用卡車急急地直駛而來。汽車嘎吱一聲停下,噌噌跳下二三十名戴鋼盔的國民黨士兵。他們挎著卡賓槍,兇神惡煞地驅趕著沿街擺賣的小攤販,沒來得及離開的小販平自無故地挨了幾個耳光,一個老漢想拾起滾在地上的水果,被一個干瘦如柴的士兵狠狠地踢了兩腳,痛苦地倒在地上呻吟。
碼頭上稍稍安靜,幾分鐘后,一輛黑色小轎車嘀嘀地駛來。士兵們把胸一挺,皮靴咔嚓一并,形成一個環形隊列,一個個表情緊張肅穆,顯然轎車上的人不是等閑之輩。
從轎車上首先下來的是中統行動隊長李剛。今天他穿一件棕黃色的云紗衫,內著一件自襯衣,小分頭梳得溜溜發亮,下車后他兩賊眼一轉,繞過車頭打開另一邊的門,接著車上推出一個背剪胳膊、五花大綁、年約三十多歲的身材高大的青年人。
他頭發蓬松,昂著頭,朝攙扶他的一個小特務淬了一口,李剛走過去一把揪住青年人的胸口罵道:“張文彬,你死到臨頭,還敢與我們作對,豈有此理!”
在機帆船的三四十米的河面上。停泊著四五只小船。戴著竹笠、一身漁民打扮的游擊隊長已經把駁殼槍的保險打開了。按照原定計劃,只等著岸上一間粥店老板的白圍裙一揚,便立刻動手。
粥店老板不是別人,正是指揮這次行動的周恩來的特派員——紅色特工“03”。
此刻,他看了下腕上的手表,嘴角緊閉。敵人正按原來的設想方案進入包圍圈,營救文彬同志行動的第一步看來十分順利。
那么,“03”是怎樣獲悉中統特務打算用機帆船把中共要人張文彬從水路押走的呢?
前兩天,“03”把方方安置在揭陽林美南鄉下的家后,匆匆趕到興寧縣城。他剛下汽車,就來到車站對面的一家酒樓,和一名以老板身份做掩護的交通員接頭,通過他與當地黨組織取得聯系,策劃營救張文彬的方案。二人接上頭后,老板把“03”帶上一間小閣樓。
這老板姓溫,在南雄工作時與張文彬多有接觸,對老上級很有感情。他對“03”介紹說:“大張個子很高,大家都叫他‘長腳’。他對人很熱情,口才很好,說話有鼓動性,吸引人,而且沒架子,很隨和,把我們當作小弟弟看待。去年夏,我在梅縣縣城街上碰見了他。他帶了一頂盔式帽,短褲長襪。我倆十分高興,找了一個地方談了很久。他叮囑我要高度警惕,要利用各種社會關系長期埋伏,等待時機。他了解我的社會關系后,要我籌劃搞一個‘紅色救濟會’,學會做些救濟工作,營救被捕同志和接濟他們的家庭,還約好了下次見面再詳細布置,并派人與我共同商量籌款事宜等等。昨天,特派員林美南通知我與你聯系,一定要把大張救出來。”
“03”開門見山地問:“大張現在關在哪里?”
“確切地點不清楚,聽說是由江西方面的中統特務專門派人看守。”老板答道。
“莊祖芳?”“03”急急地問。
老板搖了搖頭,說:“我已派人了解情況去了。”
“03”推開了關緊的木窗,一陣涼風撲面而來。他忽然發現了什么似的道:“在樓下靠東窗桌坐的顧客。咧著只大犬牙的是熟客嗎?”
老板探頭看了看,一拍手掌:“不是,他說是江西來的生意人,這兩天在這里吃過幾回飯。”
“03”凝視片刻,輕吹聲口哨:“有了,看我的。”
“03”從隨身的小皮箱里取出一套藍布長衫、一副墨鏡,三兩分鐘便成了位穿州過埠的商人。他在江西人旁邊的桌子坐下,拿出一張《中央日報》,利用眼尾的余光觀察周圍的動靜,除了江西人大嚼大咽,并無別的同伙。
江西人把半只雞腿塞進嘴里,狼吞虎咽地裝人肚里,又用舌頭添添油膩的右手,仰脖子把酒瓶里的酒喝光,吆喝道:“老板,記賬!”
老板賠著笑臉點頭。江西人打著飽嗝,哼著贛南小曲搖晃晃地走出店門口。
老板走近“03”細聲道:“他到怡紅院找相好去了。”
“03”沒吭聲,壓低駝色禮帽,跟蹤而去。
“03”靈貓般躍上有兩米多高的院墻邊的大樹,細細觀察。此時江西人在兩名妓女的簇擁下往西廂房走去,他邊走邊用手捏著一名妓女的臉蛋,哈哈大笑:“寶貝,我有錢,咱們玩個痛……快!”
“03”待他走進房間一會,嗖地跳下院墻,緊隨而入。
“03”無聲地進來,手上抓著把勃郎寧小手槍,兩名被壓在床上的妓女一見,嚇得“啊”的尖叫,急忙抓起床上的被單護住赤裸的胸脯。江西人氣喘喘地玩得正歡,見妓女掙脫自己的懷抱,咧著犬牙嚷道:“媽的,老子又不是鬼,大白天的,喊什么?”
“03”在背后冷冷地說:“自從進了中統魔窟,你就變成鬼了。”
江西人回頭一看,猛一愣,跟前站著一條威然凜氣的漢子,那神態像傳聞中的中共特工,他脫口而出:“你是‘03’?”
“判斷力不錯,不愧是莊祖芳的一頭鷹犬。”
“好啊,‘03’,你吃了豹子膽了,老子正要找你,你反而送上門來了。”那特務翻身下床,就要動粗。
“03”反手扭住他,輕輕一拍,使他兩手脫了臼;“說,你此行的目的。”
特務疼得咧牙:“不……不知道,莊祖芳沒有交待。”
“蠻像個男人似的,好,嘗嘗老子的‘滿天星’。”“03”邊說邊用食指幾個“急點”,那特務身上幾個最痛的穴位,頓時猶如刀刺火燒。他疼得眼冒金星,臉色蒼白,慘叫得連聲求饒。那兩名妓女也嚇得躲入被窩,不敢吱聲。
“你們把張文彬弄到哪里去了?”
“在……在城東一間小學校里。”
“有多少人把守?”
“六十個人,分四班,不過……”
“不過什么?”
“明天一早就要用船送走。”
“哪個碼頭?”
“韓江碼頭。”
靠碼頭的機帆船發動了引擎,發出了“突突突”的響聲,特務們推擁著把張文彬直往船上押去。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再不動手就晚了。“03”果斷地把白圍裙朝河面上一扔,隨之掏出手槍,扣動了扳機,張文彬身邊的一個特務應聲倒下。
槍聲驚動了周圍的衛兵,他們掉轉頭,端起卡賓槍漫無目標地掃射。子彈打在瓦房頂上和泥磚里,發出“沙沙”“卟卟”的聲響。幾個特務擁著張文彬朝機帆船跑去。
“打!”小艇上的游擊隊長一聲令下,敞篷大開,一挺歪把子機槍和七八支三八大蓋同時開火,幾個敵人隨之倒在水中。
“03”握著兩支德國造二十響駁殼槍站在木垛上左右開弓,兩條火舌像飛舞的銀蛇,所到之處,敵人或應聲倒下或鬼哭狼嚎……
可是一群衛兵始終死死地護衛著張文彬,重機槍在駕駛室頂上猛烈地掃射著,壓制了游擊隊的火力,兩名游擊隊的機槍手當場犧牲,其他同志也被強大火力壓得抬不起頭來,就地伏在地上。
“03”見形勢危急,大喊一聲:“火力掩護!”便就地一滾,甩出兩個煙霧彈,借著濃重的煙霧,飛身上房。幾個猴躍虎跳,靠近架著重機槍的卡車,左手一個飛拋,兩枚烈性炸彈從天而降。只聽“轟”地一聲,機槍連著卡車被炸得支離破碎。
隨著爆炸聲,游擊隊長趁敵人慌亂之問,帶著一名隊員不顧一切地跳下船,直往張文彬身邊撲去。特務行動隊長李剛一見,端起沖鋒槍猛掃,游擊隊長一個“驢打滾”躲過,而跟在后面的隊員不幸中彈,趄趔著倒下了。游擊隊長怒火沖天,朝著李剛就是一梭子,一顆子彈正中李剛的左肩胛,李剛嚎叫著倒在血泊中。
救人要緊!游擊隊長顧不了看李剛的死活,他弓著腰急跑到伏在地上的張文彬身邊,三下五除二地割掉張文彬背上的繩索,大叫著:“大張,快走!往小艇上跑,我掩護!”
豈料,張文彬忽地從懷里掏出槍,對著游擊隊長的后腦勺連開三槍,血漿四濺!
正向這邊游動想來接應游擊隊長的“03”目擊這駭人而意外的一幕,頓時驚呆了!
片刻,當聽到“張文彬”那“我打死‘03’了!我打死‘03’了”的得意忘形的叫聲時,“03”才反應過來,這“張文彬”是假的!
中詭計了!他咬著牙對著假“張文彬”一個猛掃,打得這狗特務全身都是窟窿。
“撤!快撤!“特務們背著滿身是血的李剛上了機帆船,船沒命地往下游沖去……
與此同時,興寧簡易機場,一架韶關飛機制造廠生產的中國第一批制式飛機“復興號”沖天而起。機艙上,幾名全副武裝的敵憲押著中共要犯張文彬、涂振農。
莊祖芳給坐在前艙的阿鳳點上一支煙:“阿鳳小姐,不愧是中統之花。莊某真是佩服之至,只要離開地面,共黨就奈我們不何了。他們會入地打洞我信,會下水潛行我也信,就是不信他們會上天。”
為了這架飛機,阿鳳沒少折騰,戰區司令部似乎不大買中統的帳,看著機場有飛機都說沒有,走陸路心里有是在沒底,最后是徐恩曾出面從廣西調了架飛機過來。
原來那假張文彬正是阿鳳一手策劃的。她知道張文彬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又是中共南方黨的負責人,“03”必然不會善罷甘休,她一邊放出空氣說要從水路押送張文彬,一邊又暗暗從特務中找一個身材外貌與張文彬相仿的人,用自己從美國學來的化裝術如此一番,連郭潛也真假難辨。接著,阿鳳秘密與空軍取得聯絡,決定從空中把張文彬和涂振農兩人押運到馬家洲集中營。空運計劃極為保密,連莊祖芳也才剛剛知道。
阿鳳吐了口煙圈,嘴巴一撇說:“哼,這回‘03’,不死也要脫層皮。”
“那個方方,一天不落網,我心里總是不安生。”坐在一旁的郭潛,從艙窗里俯望著云霧下的粵東大地,有點余悸地說。他知道方方是不會放過他的,這段時間他常常做惡夢,夢見方方劍一般的目光盯著他,嚇得他常常從夢中驚醒,以酒壓驚。
“放心吧,我已在粵東一帶布下大網,方方逃不出我的手心的。”阿鳳把頭向上一仰,一抹陽光照在她得意的臉上,“郭先生,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徐局長來電,準備把你接往重慶,與張國燾先生一起共商反共大計。”
郭潛大喜,禁不住掏出隨身的酒壺連灌幾口。莊祖芳不屑地“哼”了一聲。
飛機隆隆地向西南飛去,在地上投下一道淡淡的陰影。
2
獲悉營救張文彬的行動失敗后,周恩來當即發出指示,目前的形勢不宜與敵人作正面的武力沖突,應全力以赴保護方方離開粵東,盡快回到重慶,南委的工作暫停。
1942年10月下旬,方方派中共潮梅特委副特派員李平前往重慶向南方局周恩來、孔原等匯報南委事件經過和善后工作情況。
聽完匯報,周恩來指示說:“要方方在安全條件下堅決撤退,若赴渝有困難,也可去敵后,由汕頭、上海轉新四軍。”頓了一下,周恩來動情地說:“方方沒有安全離開,我一天不能安心。”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03”與方方即作去渝準備。他們先從澄海東隴把善于交際的王華生調到揭陽,利用社會關系在揭陽開了一家木炭行,正兒八經地做起生意來,以參加商會和取得“合法”身份。
1943年4月21日,待敵人的搜捕漸漸放松后,“03”辦理了進交貨、交稅和路條等手續,按照南方局的指示。選擇了經大后方赴渝的路線。
“03”把方方化裝成老板,自己裝成伙計,沿著韶關、衡陽、貴陽等地的大后方路線。順利通過各種關卡,安全回到了重慶南方局領導機關。
周恩來激動地握著方方的手,久久不語。
“03”也向周恩來報告任務完成。周恩來對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表示滿意,并嚴肅地說:“組織上決定,通過第四戰區中共特別支部的關系,把你派到國民黨陸軍大學去學習,你要長期隱蔽,打入國民黨高層機關。”
從此,“03”在江湖上銷聲匿跡,1949年10月隨國民黨陸軍司令部去了臺灣,如今若安在,也是100多歲高齡的老人了。我們應永遠記住這些在秘密戰線上戰斗的無名英雄們……
徐恩曾聞訊方方已回到重慶后,專門來電把郭潛、莊祖芳等臭罵了一頓,不過,他對于這次破獲中共南委案還是十分的滿意。他得意地對阿鳳評價說:“這是我和中共在抗戰時期戰斗中的惟一勝利。也是我的全部戰斗紀錄中經過時間最長,技術上最為成功的勝利。聽說,中共最高領導對南委破壞極痛心,說這一破壞,等于他們損失了十萬精兵。”
不過,蔣介石并沒有給徐恩曾什么好果子吃。徐恩曾是個大財迷、大官倒。他利用職權暗地里叫手下人走私緊缺物資。牟取暴利。后來被軍統的戴笠發現,向蔣介石打了小報告。說他徇私舞弊,疏于政務,結果被蔣介石撤了職,宣布永不錄用,把他趕出了中統。阿鳳的地位也隨之日落千丈,不知所蹤……
1943年6月28日,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方方隨周恩來從重慶乘飛機回到延安。在空中,方方深情地凝望著南方那縱橫交錯似有千軍萬馬在潛伏在吶喊的山嶺,感慨萬分。他默默地為在獄中的廖承志、張文彬等同志的安全擔憂,他暗暗地發誓,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回來。
遠處,晨曦已現天空。
3
南委五大常委中,郭潛叛變了,張文彬、涂振農被捕了,方方安全到達重慶,現在只剩下秘書長姚鐸還留在國統區。沒有方方監管下的姚鐸,情形又是怎樣的呢?
卻說1942年6月8日那個雨夜,姚鐸與妻子蔡瑜(南委機關黨支部書記)離開大埔,在地下黨組織的掩護下順利來到到潮陽關埠上村吳南生的家。潮梅特委特派員林美南、副特派員李平等早在那里等候。
林美南告訴姚鐸:“方方同志要我通知你,組織上決定將你轉移到蘇北新四軍處。你先在這里住上一段時間,情況穩定后,可從汕頭乘船到上海,再轉赴新四軍處。一路上會有人接應。”
一旁的吳南生將去上海的聯絡地點和8000元路費交給姚鐸。姚鐸接過后,未置可否。
林美南、李平走后,姚鐸嘟嚕說:“整個南委機關都沒了,革命還有什么意思?我才不去蘇北那鬼地方,天天行軍打仗,我可吃不消。”
蔡瑜一聽不對勁,說:“你不服從組織分配,想去哪里?”
“回家,睡大覺。”姚鐸倒在床上,用枕頭蒙住頭。
果真,姚鐸離開關埠后沒到汕頭候船趕往新四軍,而是私自回到其澄城家鄉。姚鐸畢竟是南委秘書長,又擔任過潮梅特委書記,是上級領導,林美南等拿姚鐸沒辦法,只好先安排蔡瑜在樟溪小學以“教書”為身份潛伏下來。
姚鐸是當地人,黑道白道都吃得開,“南委事件”后,政治上產生了動搖,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現在遠離組織的監督,妻子又不在家,他就漸漸地放縱起來。
到澄海后,姚鐸經常大搖大擺來往于澄海、汕頭之間,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搞在一起,與當地的國民黨政府的警察所長、區長、縣長等結交,整日花天酒地、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很快將去新四軍的路費8000元花光了。
更過分的是,他竟然包養了一個妓女阿琴,準備納之為妾,并把阿琴放在他的同學、特嫌分子陳澤波家里養著。姚鐸之妻蔡瑜忍無可忍,多次把姚鐸嚴重墮落的情況向黨組織匯報。
南委書記方方離開潮汕北上時,曾指定李碧山為南委聯絡員,保持與潮梅、閩西南領導人的聯系。李碧山、林美南等鑒于姚鐸已墮入深淵,立即將情況匯報給中共南方局。南方局領導指示馬上監護姚鐸上重慶接受審查教育。
經過商量,當地黨組織決定由鐵腕人物吳南生親自護送姚鐸上重慶。
1943年大年正月初三的清早,大霧彌漫,吳南生陪著姚鐸上路了。他們繞道興寧,經韶關、桂林等地,輾轉半個月,終于安全來到重慶,住進紅巖八路軍辦事處招待所。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熱情地接見了他倆。
姚鐸主動向董必武等領導人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劣行,董必武考慮到他能主動交代問題,還想挽救他,準備送姚鐸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誰知姚鐸聽說延安整風十分厲害,心里害怕,暗地里又早與叛徒郭潛取得聯系,便乘人不備,偷偷溜出紅巖,主動投奔中統。
對于姚鐸為什么會主動叛變,至今仍有不少謎團。據郭潛(到臺灣后改名郭華倫)寫的《中共史論》介紹,在對南委全面遭破壞的時候,“恰好在此期間,廣東調統室也曾爭取南委秘書長姚華(即姚鐸)秘密轉變,潛伏在南委內部作內線工作,遂根據內線所獲資料以及電臺聯絡時所獲之接頭地點,在粵北曲江、粵東大埔一帶,對南委各機關采取全面行動。結果除南委書記方方逃逸、南委秘書長姚華留置作向上滲透不予逮捕外,其余所有人員全部遭捕……”
如按此說法,姚鐸早在廣東已叛變。此表述真假難辨,因為郭潛在該書中只字未提自己叛變之事,看來也有其“難言之恥”。
在中統局,郭潛設宴歡迎姚鐸的到來。兩人喝高后,郭潛吹噓起來:“我進中統后才知道,早在l941年,徐局長在中統局內部成立了一個‘分化瓦解委員會’,以手下的第一號‘反共專家’王思誠為主任委員,專門從事這一類的‘心理作戰’活動,里面的成員大多數是從中共過來的。‘南委事件’發生后,徐局長知人善用,起用我為該委員會的書記,主持‘分化瓦解委員會’的日常工作。一開始,我真有點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徐老板真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有氣魄!就憑這一點我也得好好干,報答徐老板的知遇之恩!”
姚鐸小心地巴結道:“郭兄一貫有勇有謀,不知這回有何高招?”
郭潛把酒杯高高舉起:“來,喝!說實話,我鉚足了勁兒,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事業中,琢磨了幾天幾夜,終于策劃了一個‘特別行動’,對外宣告說‘中國共產黨內分裂出一個非常委員會’,并派人宣傳說‘非常委員會’已經召開了代表大會,發表了‘宣言’等。我把該計劃呈報給徐老板,徐老板連聲稱好,大張旗鼓地分派一批中統精英到重慶、貴陽、昆明、成都、西安及陜甘寧邊區周圍去宣傳,好不熱鬧。兄弟,你過來得正是時候,可以幫老哥一把,粵東這一塊就交給你了。”
姚鐸一聽,連敬三杯酒:“一切聽郭書記差遣!”
其實,郭潛沒跟姚鐸說實話。徐恩曾的確是派了一幫特務前去“放謠”,但結果發現,共產黨那邊對此毫無反應,社會上對這些“特大消息”也很不敏感。徐恩曾不禁有些失望:“看來郭潛這廝肚子里也沒什么玩意……唉,叛徒畢竟是叛徒,他以中共高干之身,而能夠甘心在我手下賣力,證明囊中貨色不過爾爾!”
此后,郭潛又“殫精竭慮”地“創作”了《新紅樓》、《某某傳奇》等兩部“謠言”大書,廣為散發,但效果仍如第一次一樣“令人失望”。
不過,姚鐸還是得到中統的重用,被委任為“廣東調查統計專員”,受廣東調統室主任陳積中領導。1944年8月,郭潛用飛機將姚鐸秘密送回廣東韶關。
由于姚鐸非常熟悉中共潮梅汕組織的情況,陳積中對姚鐸寄予厚望,任命他為國民黨中央黨部專員,化名陳繼先,其主要任務是在南方組建中統特務的反共秘密組織——“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肅清中共地下組織。接受任務后,姚鐸在韶關不敢久留,隔天便坐車經興寧,只身潛入揭陽。
揭陽位于廣東省東南部潮汕平原,東鄰汕頭、潮州,西接汕尾,南瀕南海,北靠梅州,地勢自西向東傾斜,其中部、南部和東南部都是廣闊肥沃的榕江沖積平原和濱海沉積平原,素稱“魚米之鄉”。揭陽是粵東古邑,見諸史載已有2200余年,得名于古五嶺之一的揭陽嶺,抗戰時的揭陽,是潮汕國統區的政治經濟中心,也曾是中共潮梅特委機關的所在地。姚鐸在這里工作過,自然十分熟悉。
姚鐸想到自己叛變的消息并沒有公布,便繼續以中共南委領導人的身份,假傳南方局的命令,以恢復組織活動的名義誘騙原來的老同事、老部下上鉤,籌建所謂的“非常委員會”,企圖把林美南、李碧山、周禮平等尚在活動的地下黨領導人一網打盡,徹底破壞中共潮梅黨組織。
中共潮梅地下黨,面臨著一場極為嚴峻的考驗!
姚鐸前腳剛到揭陽,林美南便收到南方局的緊急電令:“逆子不孝,卷款潛逃,注意其變賣家產。按家法處置!”
這是吳南生監送姚鐸上重慶前臨別約定的暗語。林美南由此證實姚鐸的確叛變了。
林美南,又名林子明,吳瑞麟,筆名繆南,出生于揭陽縣東園鎮東橋園村(今屬揭西縣)。1934年4月參加中共,1938年3月起任中共揭陽縣一區區委書記、縣委書記、潮普惠揭中心縣委書記、潮揭豐中心縣委書記、潮梅特派員等職。方方走后,他是中共潮梅組織最高負責人。
在傳達南方局的特急指示后,林美南斷然授命周禮平負責處決叛徒姚鐸的總指揮,執行任務的由潮澄饒敵后武裝小組,王武任前線指揮。
面對危情,林美南雙眉一揚,斬釘截鐵地道:“姚鐸的事必須馬上解決,刻不容緩!”
“好,我馬上去辦。”周禮平深知任務的重要性。
周禮平與姚鐸是澄海老鄉,對姚鐸生活習性比較熟悉。周禮平1936年10月在汕頭讀中學時,即參加潮汕人民抗日義勇軍,并在學校建立義勇軍小組,任組長。1937年春加入中共。同年“七·七”事變后,發起建立汕頭青年救亡同志會,歷任中共區委書記、縣工委委員、縣委書記等職。
周禮平很快摸清姚鐸的情況,姚鐸更名陳慶宇,公開身份是當地簡易師范學校的國文老師,他獨自住在一間寬敞的大院里,身邊并任何沒有警衛。于是,他命令鋤奸行動隊展開行動。
這是中秋前的一個夜晚,明月高懸,天氣有些悶熱。幾名行動小組成員悄然翻進姚鐸所住的院子。廳院寬敞,姚鐸正坐在竹椅上納涼,手搖一把大葵扇,悠哉悠哉地哼著一段潮劇。
“行動!”隊長蔡子明一聲令下,五名隊員呈扇形狀沖了上去。
隊員許杰首當其沖,他一個“老虎下山”,把姚鐸緊緊壓在身下,右手抓起一把大剪刀就往姚鐸身上亂刺。
姚鐸毫無防備,不知所措,下意識地把許杰握剪刀的手緊緊抓住,拼命掙扎著亂嚷:“抓賊呀,抓賊呀!”
蔡子明怕姚鐸的喊叫驚動四鄰,一個箭步沖了上來,槍口貼住姚鐸的腹部,“噗”的一槍。姚鐸頓時全身癱軟,雙手無力地攤開。
許杰用手一摸他的鼻子,沒氣了。
“死了?”蔡子明不放心,也摸了摸,真的沒氣了。其他三名隊員也上前,跟著摸姚鐸的鼻孔,都搖搖頭道:“死定了。”
“撤。”蔡子明放心地命令隊員們撤退。
隊員們高興地回到隊部所在地佘厝洲,向周禮平匯報成功處決姚鐸的經過。周禮平沒想到這么容易就把姚鐸干掉了,高興異常,但還是有些不放心地問:“真的死了嗎?不會裝死吧?”
蔡子明擺著手道:“死硬了!我和許杰等都摸過他的鼻孔,真的沒氣了!”
但是,姚鐸并沒有死,那一槍下去,他立即屏氣凝神裝死。行動小組撤離后,姚鐸大喊救命,被鄰居送往醫院,死里逃生,撿回了一條命。
姚鐸放出狠話:“我不死,就會有很多人要死!”
4
姚鐸傷愈后,被安排住進國民黨揭陽縣黨部書記長陳偉烈的堂弟、特務頭子陳廊梁的家中。那是一座老式兩進的大院子,兩扇油光黑亮的大門襯托著高墻深院,十分氣派。特務們給姚鐸派了一個專門的保鏢,并安排一個老大婆照顧人的起居。另外,還有一對姓黃的夫婦住在院子中。
姚鐸深知共產黨懲處叛徒的厲害,第一次行動失敗,必有第二次。他成天蝸居在院子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口袋里總揣著一支裝滿子彈的勃朗寧手槍。
這樣的日子過了十天半個月,姚鐸又閑不住了,隨著身體的康復,他的色心又起。他是一個離不開女人的好色之徒,可是他又不敢上街去找妓女,一來怕再遭刺殺,不安全;二來身染梅毒,也不敢再找不干凈的女人啦。怎么辦?
姚鐸想起了在潮陽一中教書的惠姑娘。
惠姑娘叫陳德惠,是一位秀外慧中的典型潮汕女孩。她中等身材,留一頭秀黑的長發,圓圓的臉上總蕩著天真爛漫的笑容。她原是南委機關的資料員,與方方夫婦在一起。姚鐸當時并不認識這位女孩。只是兩年前隱蔽到汕頭之后,才見到這位女孩,一下便被她迷住了,真有點相恨見晚。
惠姑娘告訴姚鐸,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早知道姚秘書長是“一支筆”,常以姚謠的筆名在南委機關報上發表文章,很是仰慕。姚鐸一聽,引以為知音,隔三差五地就來找惠姑娘,并以南委領導人的身份,借著談工作,約她到茶樓喝茶。一來二去,兩人熟了。姚鐸得寸進尺,竟然提出要惠姑娘跟他結婚,惠姑娘一聽,斷然拒絕道,姚先生你已有妻子,我也快與我的未婚夫結婚了,咱倆沒戲。
現在,姚鐸正籌建組織,最希望的有惠姑娘這樣才貌雙全的人做他的助手,那可是一舉兩得。他估計,只要惠姑娘肯留在他身邊,得手就是遲早的事了。得手就行,結婚也就是順口說說而已。
于是,他試著給惠姑娘寫了一封邀請信。信發出去大半個月了,既沒見到惠姑娘的蹤影,也沒見到她的回信,姚鐸不覺有些失望。其實他盼惠姑娘來,又怕惠姑娘來。他擔心惠姑娘真的來了,卻是周禮平派來的臥底,專門來刺殺他這個叛徒的。
正在矛盾中時,負責照顧他的老太婆來報:“門口有兩位姑娘執姚先生的信求見。”
“快快請進。”姚鐸猜是惠姑娘,喜得彈跳起來,但他又不忘給保鏢丟了個眼色,保鏢立即把槍上膛,躲在一側。
進來的果真是朝思暮想的惠姑娘,身邊還有一個中學生模樣的女孩。
兩年沒見,惠姑娘更加光彩照人。姚鐸眼睛驀地一亮,高聲叫道:“啊,德惠,你真的來了!好好,這位小妹是——”
惠姑娘笑盈盈地說:“這是我的四妹陳德鴻。”
“喲,長得跟你一樣,麗質佳人嘍!”姚鐸連忙請惠姑娘姐妹到客廳里坐。
寒暄幾句后,姚鐸試探著問:“世道不穩,惠姑娘大老遠來看我,姚某真是三生有幸。”
“姚先生,是這樣的,接到你的信后,沒過幾天,剛好梅興中學就給我發來聘書,要我去任教。我曾在梅縣教過幾年書,教的是數學課。今天,我就帶著小妹前去應聘,小妹跟我到梅興中學讀書。我順道來看望你。”惠姑娘解釋道,望了望姚鐸有些浮腫的臉,關切地問,“你怎地,臉色黃黃的,生病了?”
“哎喲,德惠,你姐妹能來看我,我十分感激。你不知道,我不久前得了一場大病,險些不能見到你了。”姚鐸把惠姑娘的聘書接過來仔細看了看,見沒什么破綻,便挽留道,“我看你還是留下來吧,代我的課,待我身體好了,你要往梅興去,你妹妹也可在簡師就讀,你看行不行?”
“這不行,我可是答應了人家的。”惠姑娘以簽約在先,任憑姚鐸如何勸說,死活不肯留下。
姚鐸急了,到手的鴨子豈能讓它飛了?他又請惠姑娘的父親出面來勸,陳父見姚鐸言辭懇切,又不知姚鐸的真實身份,也勸女兒留下。惠姑娘畢竟是心軟的女孩,經不起姚鐸的左纏右磨,終于答應留下來幫姚鐸代課,待他病情好轉后,再去梅縣。姚鐸大喜過望,安排她姐妹倆住下,千方百計地博取她的歡心。
姚鐸幾乎每天都來看惠姑娘一次,但他夜間不敢來,都是白天來,口袋里仍帶著手槍,后面跟著保鏢。每次姚鐸陪惠姑娘散步,保鏢都在后緊跟著。
有一次,惠姑娘回頭瞧了瞧,不高興了,嗔怪道:“真討厭,跟你這人交朋友很討厭。說句悄悄話后面還跟一條狗!”
姚鐸一聽,回頭便對保鏢說:“去去去,以后我跟陳小姐出門,你就別跟了!”
那保鏢如遇大赦,一溜煙就不見人影了。
姚鐸見四下沒人。想抱惠姑娘,誰知身子一靠近,惠姑娘就碰到他口袋里硬邦邦的手槍。她嘟著嘴,生氣道:“瞧你,跟我在一起還帶著槍,礙腳礙手的,走火了,還會傷人!真討厭!”
姚鐸準備近期到重慶向郭潛匯報工作。他想帶惠姑娘一同前往,又怕惠姑娘不跟他走,另生變故,欲火中燒的他,忘了一切,對惠姑娘百依百順。自此,他和惠姑娘在一起,就再也不帶手槍和保鏢。
兩人交往了半個月,姚鐸的戒心漸漸減弱。轉眼到了1943年11月12日,這是個星期天,下午2時多,秋陽高照,姚鐸來約惠姑娘姐妹去飲午茶。惠姑娘欣然答應,還說今天是個好日子,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等惠姑娘換好衣服下樓時,那身打扮讓姚鐸雙眼放光:身穿白底藍小花旗袍,外套一件咖啡色外套,腳蹬咖啡色半高跟皮鞋,光滑的小腿漏得恰到好處。
他們三人來到榕江邊一間雅靜的茶室。江風輕拂,茶香醉人。姚鐸十分健談,從天上說到人間,神采飛揚。興致高漲時又在惠姑娘相勸之下開了瓶酒,一時間軟風微醺,心旌搖搖,姚鐸已經把持不住自己的眼睛,沖著惠姑娘姐妹身上到處亂看。
喝完茶,已是下午三點多一點,喝得都有點困意了,惠姑娘瞪著水靈靈的大眼睛認真地看著姚鐸,姚鐸被看得浮想連天,問:“惠姑娘是不是有話說啊?”
惠姑娘卻提議說:“陽光這么好,不如你陪我散散步,順便到城外的商業學校,看望我的老同學鄭仁聲。我來揭陽要半個月了,還沒見過他。”
姚鐸沉吟不語,心有顧慮,因為商業學校雖然離城不過一公里,又是大白天,但自己既沒帶保鏢又沒帶槍,路上有個萬一怎么辦?
“去嘛。”惠姑娘嬌嗔道,冰雪聰明,看出了他的顧慮,說:“要不,再邀簡師幾個女生一起去,好嗎?”
大概人多勢眾能給他自己壯膽,再加上有幾個漂亮女孩嘻嘻哈哈陪他出游,正合他意,姚鐸欣然答應了。于是,他們三人返回簡師,邀了兩個姚鐸最信得過的女學生。
三時半左右,他們一行五人,離開簡師,往商業學校方向走去。一路上,大家談笑風生,身材瘦長的姚鐸在眾女孩的陪同下格外顯眼。
進賢門是揭陽古城的標志性建筑,在揭陽“古八景”中被稱作“譙樓曉角”。進賢門位于揭陽城東、北二城門之間,始建于明代天啟元年(公元1622年)。整個建筑古樸大方,是潮汕古城門建筑中的佼佼者.明、清時期,城樓上設有更夫,每當殘月西斜,晨曦初現,更夫吹響報曉號角,角聲隨晨風傳遍全城,“譙樓曉角”因此得名。
進賢門下是個喧鬧的市場,各種叫賣聲不絕于耳。姚鐸一行沒有停留,說笑著穿過進賢門。門外比城里僻靜些,有一片剛收割的稻田,不遠處就是商業學校的大門,旁邊的操場正在舉行籃球比賽。
忽然,一個穿便裝的青年漢子從左側田地里快步斜插上來。姚鐸一愣,見那漢子只是朝前直走并沒有任何異動,他又鎮定地繼續前進。
正在此時,那漢子猛地一轉身,從懷里拔出手槍,瞄準姚鐸“叭”地就是一槍。姚鐸下意識地伸出左手一擋,正好擊中虎口,鮮血直流。
那漢子猛扣第二槍,但子彈卡殼了。姚鐸一見,急忙飛步上去奪槍,并大聲叫道:“捉賊喲,捉賊喲!”
這呼叫聲驚動了廣場正在觀看球賽的群眾。眾人紛紛圍攏過來。
另一漢子見狀,從前面沖過來,對準正逃往商校廣場的姚鐸“啪啪啪”連發三槍。這三槍都打中姚鐸。但他并沒有倒下,踉踉蹌蹌地直奔商校校園中。那兩個漢子在后面緊追不舍。
惠姑娘姐妹倆愣了一下,跟著跑進商校。另兩個女學生嚇得花容頓失,大叫著飛跑回城里報信。
這是中共潮汕地下黨精心策劃的鋤奸行動。惠姑娘正是行動小組負責人周禮平派到姚鐸身邊、配合這次行動的關鍵人物。
當獲悉姚鐸叛變后,惠姑娘義憤填膺,她毅然決然地接受了周禮平設計的“紅色美人計”的安排,一步步地取得姚鐸的信任,并把他引入這伏擊圈。剛才,開第一槍的正是行動小組成員陳應銳,綽號阿五;另一個開槍的,是行動小組成員李亮,綽號阿六。
姚鐸忍著巨痛,奪命逃入商校右廂一間廚房內,隨手“呯”地一聲把門關上。
阿六飛步直追,一腳把廚房門踢開,只見姚鐸癱倒在屋子里,便二話不說,揚手就是一槍,擊中他的下腭,姚鐸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緊追其后的阿五怕姚鐸又跟上次一樣裝死,要阿六再補上幾槍。阿六又“啪啪啪”往他腦袋打了幾槍,便催阿五道:“撤吧,他腦袋開花了,全身開花了,大仙也無法起死回生。”拉著阿五就要往外走。
“不不,再待一會兒,待他身體僵硬了再走,反正任務已完成,早走慢走都無妨。”阿五已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可不能再犯上次的錯誤了。他會害死我們好多同志的。”
阿六再勸道:“走吧,阿五!”阿五見姚鐸真的死了,才放心地走出廚房。
他倆走出門口,有一個婦女從院子里跑出來,大叫:“殺人啊,殺人啊!”她這一嚷,打球的師生朝阿五、阿六圍攏過來,見他倆有槍,都不敢靠得太近。
阿五見惠姑娘姐妹倆也站在圍觀群眾中四下觀望,便有意看了她倆一眼,話中有話地嚷道:“冤有頭,債有主,此事跟你們無關,回去吧!”
惠姑娘會意,立即拉著妹妹離開商校,回到簡師住處。
而阿五、阿六迅速撤出商校,沿著長堤直奔岐河渡口。岐河渡離商校有三公里,這里江面開闊,江心有河洲,蘆葦叢生。他倆來到渡口,見有一條空船靠在岸邊,船夫在樹下打紙牌,就急令船夫,強行搭船過江。
船剛搖動,后面便傳來“抓住他倆,抓住他倆”的呼叫聲,隨即是“噠噠”的槍聲,子彈呼嘯著從他們的頭頂飛過來。他倆叫船夫快搖。
追到岸邊的國民黨兵見船不肯停下,便架起輕機槍、卡賓槍向渡船射擊。阿六形勢不妙,便嚷道:“阿五,跳下!”說著,他與船夫“通通”跳下水。而阿五為了掩護阿六和船夫,竟一躍跳上江心的沙洲阻擊追兵。
“給我打。”岸上的軍官發現目標,指揮火力向阿五射擊,一顆子彈射中阿五的大腿,他“哎喲”一聲,栽倒在沙洲的稻田中。
阿六浮出水面,見阿五中彈,急忙道:“阿五,傷在哪里?”
阿五大聲道:“傷在大腿,你趕快走,不要管我!”
這時,國民黨兵劃著另一條船追了上來,密集的子彈直向他倆射來。阿六一咬牙,潛入水里。
阿五為了掩護阿六,決心把敵人的火力引向自己。他在沙洲破口大罵:“狗雜種,有種沖過來吧!我夠本了,我跟你們拼了!”
“啊,在那里,給我狠狠地打!”有一個當官的聲嘶力竭地吼叫著,密集的雨彈射向阿五。
阿六已逆向游回靠榕城的岸邊,知道阿五為了掩護他,把敵人的火力引向自己身上。英勇地獻出了生命。他心內一陣絞痛,用手狠狠抹去滾滾的熱淚,用勁游上岸去。
阿六安全脫險后,向阿五的妻子陳錦含淚敘說了阿五英勇犧牲的經過。
陳錦禁不住失聲痛哭,但她跟阿五生活多年,深明大義,擦干眼淚對阿六道:“阿五犧牲了,他死得值,。為黨鏟除了這么大一個禍害,他會閉眼的。”
姚鐸死后的第三天,國民黨當局以揭陽簡師名義為姚鐸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數天后,當地《汕報》上登了一則新聞,說揭陽教員陳慶宇因三角戀愛被人槍殺身亡。惠姑娘則帶著妹妹,在中共地下黨的掩護下,安全撤離揭陽,往粵北跟其未婚夫老熊結婚,圓了他們六年相思的夢。
郭潛知道姚鐸死后,陡生兔死狐悲之感,從此,他不再敢到一線去抓共黨,又改了名字,躲在中統機關大院里研究共黨情報和中共黨史。


掃一掃,關注廣東殘聯微信